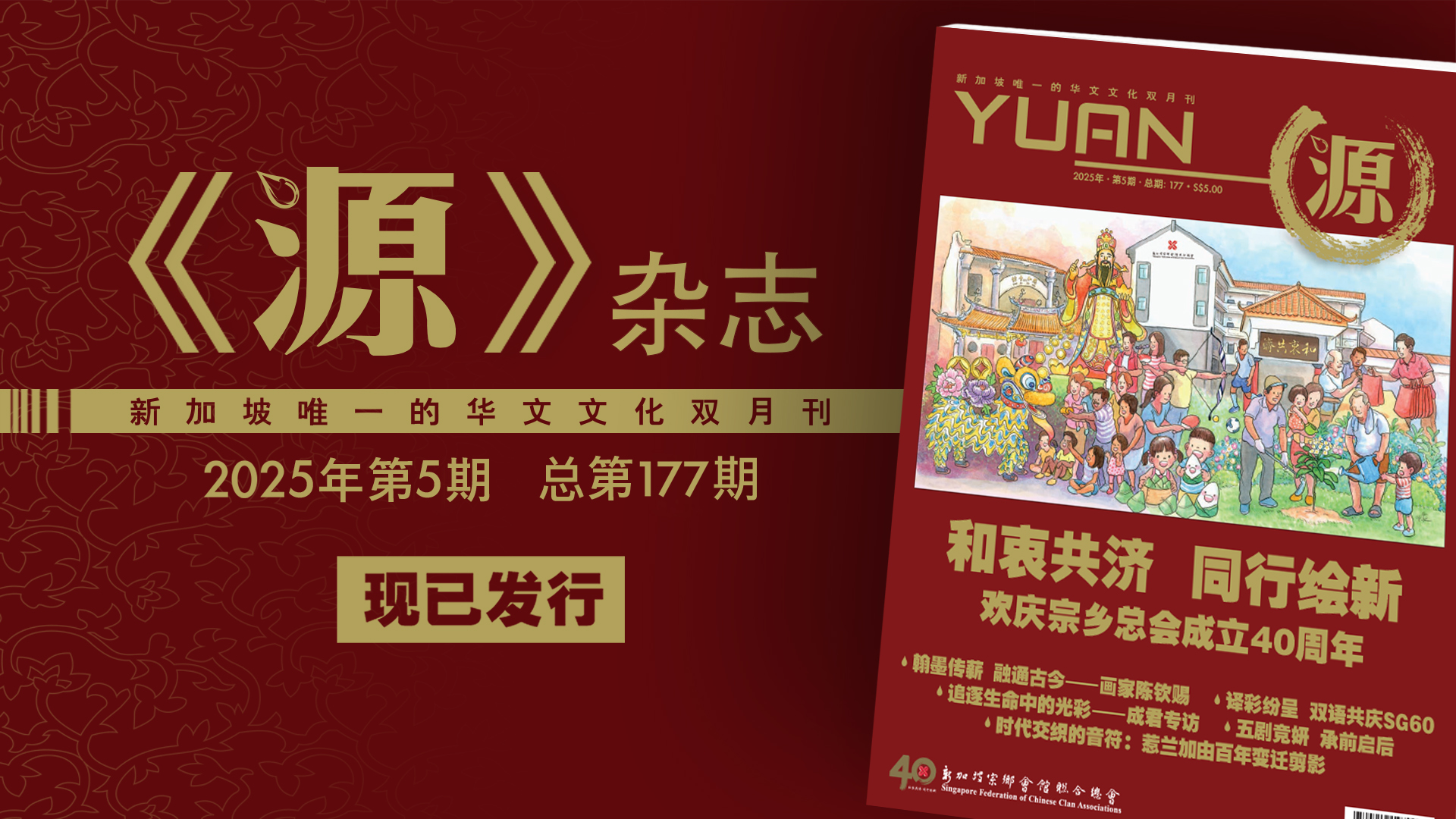以艺术的距离感介入并表达
——画家巫思远
文图 · 赵宏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论述艺术的双重本质——社会现实与自律性时指出,“艺术奉献给社会的不是某种直接可以沟通的内容,而是某种非常间接的东西,那就是抵制。从美学意义上讲,这种抵制导致社会的发展,而不是直接模仿社会的发展。激进的现代派艺术之所以保留着艺术的固有禀性,是因为艺术让社会进入了自身的境域;不过,这里只是借用一种隐蔽的形式,就好像是在做一场梦那样。倘若艺术拒绝这样做,那它就会自掘坟墓,走向灭亡。”[1]
在新加坡,就有这样一位用冷静思考,表现社会的画家——巫思远(Boo Sze Yang,1965- )。他用艺术保持一种相对的距离,但他对社会的介入却是认真、直接而且敏感的;他似乎是一位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但并不张扬,不是情绪化地手持长矛冲向魔鬼般的风车,而是安静、娓娓道来,就像一位有着崇高志向和信仰的、来自偏远山区的乡村教师。在他身上,有着一种特殊的融合气质。我们不能过于随意地把巫思远归入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范畴,抑或是曾经时髦一时的波普艺术。他是一个混合体,他的作品也与那些风花雪夜式的“为了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有明显的区别。即使他用凌乱的线条画一座商场、一座教堂,抑或别的什么,人们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带有主观介入的、批判式的表达。
在求学中遇到灵魂拷问
巫思远祖籍潮州普宁,家族中人多从事造船业,没有人学习美术。他是长门长孙,从小就受疼爱,父母也从不给他压力。在学校,他各科成绩一般,只有美术最好。虽然在英校读书,但华语流利,热爱华文,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亲近感。中学毕业后,他先是遵照惯性思维去义安理工学院读造船专业,但终究无法说服自己的内心,转而投向美术。1988年起开始修读南洋艺术学院预备班,一年后正式入读,1991年毕业。
1995年,巫思远赴英国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修读研究生学历课程,为期9个月。导师在课上讨论分析他的作品时,称赞他技巧不错,色彩也很好,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令他深感触动:“在这些作品中,我没有看到你。”[2]彼时巫思远的作品主要是受到西方超现实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及混合媒体等表现手法影响。他在学校里学到的就是这样的西方艺术,也因此以为那就是他应该遵循和向往的艺术。然而在英国教授眼中,那些作品充其量只有技巧可言,看不到与他所代表的新加坡华人的文化概念的任何关联与艺术想象。在当时的历史景观之下,文化的差异性依然是欧美主流文化精英阶层所关注的话题。在殖民主义全面崩塌的196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里,西方人敏感地看到曾经弱小的国家或民族的逐渐崛起或文化复兴,也因此充满了深具旁观者心态的兴趣和观察,而绝大多数像新加坡这样的在历史上并不十分清楚或不能十分明晰地表白自己文化属性的国家,还处在文明归属的觉醒与半觉醒之间徘徊,只好沿袭旧时的文化倾向和态度。这在原本高高在上的西方文明体系看来是颇为疑惑不解的。

《歧路》, 布面丙烯, 208x190cm,1995
对巫思远来说,这是一个击中内心的重要问题——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身份是什么?面对这一灵魂拷问,巫思远于同年创作了一幅与以往风格完全不同,介于抽象和具象表现之间的作品《歧路》。
从1996年开始举办第一次个展开始,巫思远一直都在思考绘画的本质这个问题。他关心周围熟悉的事物,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触摸到心跳。期间他在南洋艺术学院教书,从初级素描到三年级学生的创作,同期也每年举办一次个展。2003年,他再次踏上求学的旅程,赴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Chelsea College of Arts,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学习,2004年获得硕士学位。这是一次近乎朝圣的历程,他终于去了一直想去的地方,那里也是他在南艺时的校长林友权曾经读书的地方。
时过境迁,巫思远发现美院的教授们不再关心8年前提出的文化身份的问题。世界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欧美的美术主流已经将艺术还原到艺术本身,绘画再一次重新回归到纯粹的绘画本体,一切似乎都变得简单和原始了。但此时的巫思远已经成熟,不可能就这样再次被盲目导引着回归。以前,他把思考放进画面与社会沟通,多少有说教的意味。现在,他通过画面本身进行交流,激发别人的思考,不再主动把思想放进去,而是用画面把他所思考的东西导引出来,因之更具有思维的流动性与伸缩性,更宽容。返回新加坡之后,巫思远一边继续教书,一边埋头创作,于2009年获得新加坡大华银行全国绘画比赛白金奖项。
艺术的使命是唤醒和反思
2015年,巫思远决定结束在南洋艺术学院的教书生涯。十几年的稳定工作让他可以安心走过艺术的成长历程,不必过分忧虑生活压力。此时他要单纯地做一名职业画家,花更多时间在绘画创作上,以独立艺术家的身份,用艺术的使命去唤醒而不是讨好别人。他很认同墨西哥文学家克鲁兹(Cesar A Cruz)的说法,“艺术的职责是让那些过得舒适的人不舒服,也安慰痛苦的人”。
巫思远的创作主题非常广泛:从平凡的家居静物到天主教堂辉煌壮丽的内部装饰;从购物商场颓圮的空间到政治人物的表情瞬间。在他看来,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物件、静寂的建筑内部结构,都是人类生存舞台的环境道具的镜像。他以看似凌乱却深含哲理的笔触,以及略带忧郁和偏执的色彩,创造出纷繁迷乱、暗含毁灭的空间气氛,以及不可预知的末世景象的玄思。他眼中的风景,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建筑,这很符合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国家的自然属性。他将曾经富于情感表达的、画布上的英国式的自然风景,转化成一系列的、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森林一般的城市建筑城。画面上的建筑仿佛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在移动或颤抖。不规则的线条和有意识地偏转的透视痕迹,构建出梦幻般的图像,在抽象和具象的边缘,演绎现代社会人文的矛盾性及不可预测性。
巫思远的另一类重要创作主题则是一些颇具社会暗喻意义的、类似于政治波普的绘画。他用明显的、几乎是黑色幽默和夸张的戏剧性解构手法,创建了一系列具象绘画,探索人们对真理和现实世界的感知。他说,谎言就是化装舞会的真理。这样的观点与阿多诺的理论形成一定程度的契合。阿多诺认为:“自律的艺术作品是反思性的”,“它并不诉诸于声嘶力竭的宣讲,抑或主体的移情和认同,而是通过微妙曲折的方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处境,进而反思并寻求改变现实。这种审美教育确立了读者与艺术作品的距离感,终结了所谓净化、升华和移情等传统接受模式——这些接受模式客观上具有为现状辩护的意识形态效果。在此意义上,艺术也就具有了实践性。”[3]
-600x479.jpg)
《又干掉一个》 , 亚麻布上油画, 120x150cm. 2021(私人收藏)
阿多诺认为艺术的自律是艺术介入的前提,“艺术的二重性”是逻辑起点,即指艺术兼具自律性和社会性,艺术通过打破与社会的边界完成对现实的干预或介入。2021年,巫思远创作过一幅名为《又干掉一个》(《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的亚麻布上油画作品。作品的英文名称引自英国皇后(Queen)摇滚乐队发行于1980年的一支金曲,主唱是红极一时的弗雷迪·默丘里(Freddie Mercury,1946-1991)。为了录制这首歌,据说弗雷迪甚至把喉咙都吼出了血。该曲曾一度三个星期登顶美国流行金曲排行榜冠军,销量达到惊人的700万张,歌中接近结尾的地方,会反复重复这一句歌词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又干掉一个)。
巫思远的用意显然不在于歌曲所演绎的故事。画面中三个身着绿色军服和黑色长靴的军人正在异常投入地舞蹈,大檐帽掩盖了军人的表情,但肢体的动作却出卖了一切,舒展、夸张,得意的气氛不言自明,背景则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画面中军人的形象似乎没有明确的指引,无法辨认是属于哪个时代、哪个国家?但显然可以看出,三个军人在庆祝一场杀戮的胜利。
在西方油画语境里,三个一组的形象排列是有特殊的含义的,尤其是宗教的意味。通常是“三美”,由裸体的女性组成,取材于希腊神话的美惠三女神,文艺复兴以来最出色的艺术家几乎都创作过这一题材的作品。在巫思远的画框中,女神变成了军人,虽然他们的手里没有杀人的手枪,也看不到鲜血,但火焰和他们恣意地舞步,已经泄露了刽子手的身份。这里记录的显然是对于追求和平的人们的暴力镇压。巫思远用极具嘲讽和幽默的笔触,讲述了痛彻心扉的悲凉与黑暗——画面充斥着欢乐与光亮的火焰,却让人看不到一丝光明与安慰。这是一幅有相当政治波普意味的作品,在相对保守的新加坡却得到了积极市场响应,一经完成即被某知名头家收藏。从侧面体现了新加坡本地对批判题材艺术作品的极大包容,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令人欣慰。
创作题材的变换和解构
巫思远的创作是一种进行时态。他对社会的观察角度在变,他的创作题材也随时为之改变,每一次转换他都见解深刻、得心应手。在建筑系列作品里,他有两类作品颇引人注目:一类是新加坡的大型商场,一类是教堂。
-600x449.jpg)
《罗马圣彼得大教堂》(VIII), 亚麻布上油画, 112.5x150cm,2010 (私人收藏)
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Saint Peter’s Basilica,Rome》)这幅作品中,巫思远以独特的视角、构图与色彩组合,完成了一件不同寻常的、超越世俗精神世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也称圣伯多禄大殿,是位于罗马梵蒂冈的天主教宗座圣殿,是天主教会重要的象征之一。教堂作为最杰出的文艺复兴建筑和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最多时可容纳超过6万人,中央穹窿的直径达42米,顶高约138米,被视为是天主教会最神圣的地点。巫思远的内心是强大而独立的。他没有像卑微的普通人或虔诚的教徒那样对这座有着高度精神内涵的建筑直接跪拜,而是以建筑师的眼光和手法,对客观存在的现实建筑,在画布上完成了超越现实空间的解构定位——用两组大笔触弧线切割了画面的正上方和右下方,偏转了固有的、具有超强稳定性的三角直线构图。然后在画面左下侧填充罕见的、大面积的黑色颜料,用刮刀划出梁柱和雕塑装饰组件的大致轮廓和高光效果,由此在画面上重新建立了以体积为基础的三角关系。
这种构图方式是大胆的,具有极为震撼的视觉效果,把观众的视角直接切入到这座教堂最壮丽的部分。同时,他没有过多地使用表现真实的色彩,而是选择夸张的、情绪化的黑色和黄褐色,间接把白色标记为天窗和高光部分,整件作品的气氛凸显出一种神秘感和另类的压抑感。此时,教堂代表的不再是通常人们所乐于见到的华丽、神圣、高雅、庄严的气质,仿佛升腾起一种摄人心魄的、无法抗拒的力量。这力量也许并不来自导引凡人走向天堂的温暖之手,而是带来死亡和恐怖的冷漠,萧然肃穆,无法反抗。
在表现人物内心方面,巫思远达到的高度也是一般画家难以企及的。他创作过一组以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为主题的作品,使用类似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特有的粗犷、犀利、具强烈暴力与梦境般的图像抽象表现主义手法,凸显主题人物的内心与普通观众心理观感,令人印象深刻。
“在文化工业愈发繁盛、纯粹艺术愈加陷入危机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艺术要想有益于世道人心、介入社会历史进程,就必须是具有整一性审美形式的自律艺术。它并不诉诸于声嘶力竭的宣讲,抑或主体的移情和认同,而是通过微妙曲折的方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处境,进而反思并寻求改变现实。这种审美教育确立了读者与艺术作品的距离感,终结了所谓净化、升华和移情等传统接受模式——这些接受模式客观上具有为现状辩护的意识形态效果。在此意义上,艺术也就具有了实践性,完成了对现实的介入、沟通和交流。”[4]
》-黄麻布上油画-180x180cm,2011(私人收藏)-600x602.jpg)
《商厦#19(狮城大厦)》, 黄麻布上油画, 180x180cm,2011(私人收藏)

《梦的地平线#3》, 亚麻布上油画, 100x80cm,2024
注释:
[1][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2]巫思远,《Boo Sze Yang, Forever at the Crossroads》,Sunda Press Singapore,2015.
[3]常培杰,《阿多诺对“艺术介入”的批判》,《哲学动态》,2015年第6期。
[4]同注释[3]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Boo Sze Yang, A Humanistic Painter
In Singapore, there is an artist, Boo Sze Yang, who expresses his feelings and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society directly through his artworks. Art helps him to maintain a relative distance, but his involvement in society is direct, serious and sensitive; he seems to be a Don Quixote-like character, but unostentatious nor emotionally holding a spear and rushing towards the devilish windmill. Instead, he is quiet and eloquent with a calm mindset, just like a teacher from a remote mountainous area with lofty ambitions and beliefs. He has a unique fusion temperament, which cannot be classified under the categories of realism or critical realism, or the once-trendy pop art. He is a hybrid. His artwork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vast majority of romantic “art for art’s sake” paintings. Even if he uses messy lines to draw a shopping mall, a church or something else, every viewer is able to sense his subjective intervention and critical expression strongly.
Boo’s creative themes are very wide, from ordinary household still life to the magnificent interior decoration of Catholic churches, from the dilapidated space of shopping malls to the expressions of politicians. In his point of view, mundane objects and the quiet internal structures of buildings are all mirror image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ps on the stage of human existence. With his seemingly messy yet philosophical brushstrokes, and a slight tinge of melancholy and paranoia, he creates confusion, an atmosphere which signifies destruction as well as a metaphysical thought of unpredictable apocalyptic scenes. The scenery in his eyes is the buildings in daily life,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nature attributes of a city state like Singapore. He transformed the British natural landscapes on canvas, that once emotionally expressive, into a series of forest-like urban architecture that are inevitable in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buildings on the paintings do not seem to be static, but moving or trembling. Irregular lines and consciously deflected perspective traces construct a dreamlike image, interpreting the contradictions and unpredictability of modern social humanities on the edge of abstraction and figuration.
Another theme of Boo’s creations is social metaphors similar as that of political pop art. He uses distinct, exaggerated dramatic deconstruction techniques close to black humour, to create a series of figurative paintings to explore people’s perceptions of truth and reality. He has applied Francis Bacon’s unique rough, sharp, violent and dreamlike abstract expressionism techniques to highlight the inner world of the subject characters and the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s of ordinary audiences, which is impressive. In terms of expressing the inner world of characters, Boo has reached a level tha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for painters generally. His perspective on society is changing and his creative themes are also changing at any time. His creativity is progressive and every change is insightful and handy. In the architectural series, he has two categories of works that are quite eye-catching, one is the large shopping malls in Singapore and the other is the churc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