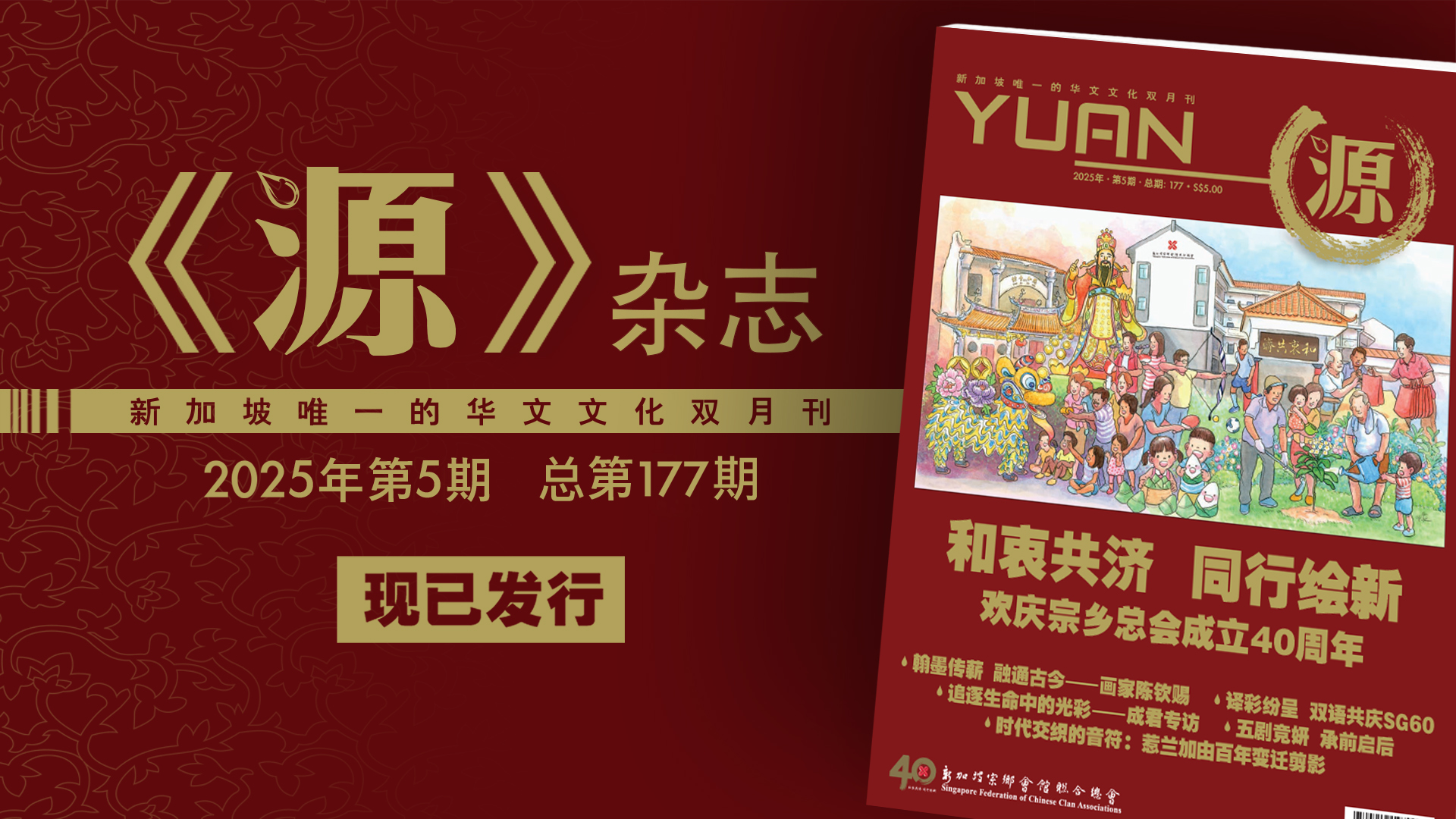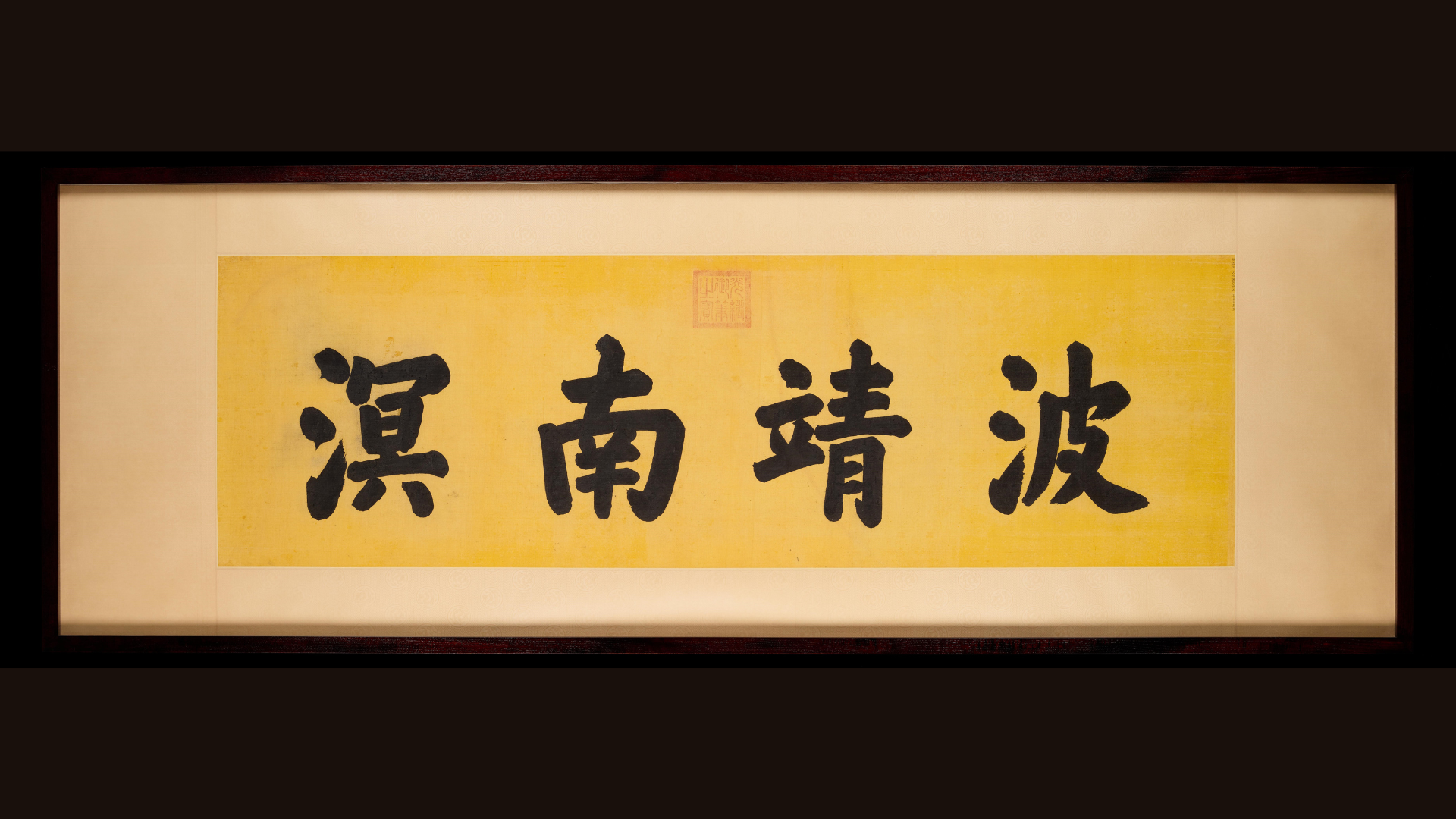理性王国 诗意飞扬
——廖建裕专访
文 · 齐亚蓉 图 · 受访者提供
第三代土生华人
1941年2月21日,印尼雅加达市丹那望区。一大早,一声婴孩的啼哭回荡在一家地砖厂隔壁的住宅区上空——经营该地砖厂的廖先生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他给这个排行老三的男孩取名建裕。
建裕的祖父十来岁时自福建安溪南来闯荡,祖母为土生华人(早期迁居至东南亚一带的中国移民跟当地土著通婚所生后代)。建裕的父亲年少时曾被送回厦门,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读过几年书,长大成人后,他也娶了一位土生华人为妻,他们的孩子当属第三代土生华人。
虽然会讲华语跟流利的福建话,但廖先生从来不用华语或福建话跟孩子们沟通,他们的家庭用语是雅加达方言或印尼语。
五岁左右,未曾进过幼稚园的建裕被送入丹那望中华学校,这个自幼跟土著工人子女为伍的第三代土生华人开始接触华文。
从新华到巴中
进入丹那望中华学校之后不久,建裕即转入新巴刹中华学校(简称新华学校或新华),建裕的两个兄长及一个弟弟也就读该校。父母担心他们的华文赶不上,专门请了家教上门给他们补习。建裕很快便对华文产生了兴趣,他在书写方面的进步尤为显著。
进入高年级之后,建裕便到学校图书馆借华文书来读。除了各类民间故事、神话及童话故事,他也喜爱改编自《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的连环画。此外,他还常常自己买课外书,《世界儿童》是他最为喜爱的读物,后来,他还写文章投稿至该刊物发表。
除了中文书刊,建裕也喜欢读印尼文故事书。每逢周末,他便到住家附近的印尼书店及小书摊浏览或购买印尼文刊物。
跟同龄学童一样,建裕也喜欢听故事。教他中国语文并给他当过班主任的何学如老师是一位讲故事高手,他常常在下课前十分钟开始给学生讲故事,每到精彩之处,下课铃声随即响起,同学们无不翘首期盼他的下一堂课。有一天,当建裕得知何老师讲的部分故事题材取自世界名著《爱的教育》时,他即刻跑去图书馆借阅,可惜晚了一步,该书已被别的同学借走。那天傍晚,他马不停蹄跑去一家华文书店买了一本回来,一口气读完之后才安然入眠。
1952年下半年,年仅11岁的建裕升入新华学校初中一年级(他跳过级,在新华小学只读了五年即毕业)。
初中生建裕最为喜爱的科目当属华文与历史。此时的他在华文老师詹庆祥的影响下开始读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丹娘》《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及中国的报道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译述印尼民间故事投稿给《世界儿童》杂志,后来,他还投稿给雅加达的《中学生》月刊。
初中三年级时,他萌生了为雅加达的左翼中文报《新报》及《生活报》投稿的念头。那年下半年,他写了一篇有关阿飞的文章,并以本名投给《新报》副刊“小新报”。1952年2月的一天,那篇写阿飞的短文在《新报》刊出,次日,他在校门口附近受到几个阿飞的“警告”。建裕并未因此而放弃写作,不过他在行文之时更加谨慎。除了本名,他也开始用笔名谷衣(裕也)发表文章。
初中毕业后,建裕考进由印尼侨领司徒赞等人创办的华侨名校——华侨公立巴城中学(简称巴中)。
巴中学风严谨,招考严格,加之师资力量雄厚,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学生。除了注重学业成绩,该校的文艺气氛也相当浓厚。进入巴中不久,建裕即加入了校内的黑板报小组,为黑板报书写短稿。除了继续在《新报》副刊发表诗歌、短篇小说跟散文,他也在《生活报》撰写杂文跟影评。
自1951年起,巴中的华侨子弟即掀起了回国升学的热潮,作为“华人”的建裕则在高中毕业后选择报考新加坡的南洋大学。相对于其他人的“北上”,他戏称自己“南下”。

1955年,廖建裕(后排右三)与父母、兄弟妹妹合影
高校岁月
1959年1月,建裕跨入南洋大学的门槛,成为该校中文系的一名学子。
甫一入校,他即开始在《大学青年》杂志上发表译作。这是由高他两届的周粲及高他一届的黄孟文负责编辑的文学刊物,建裕跟这两位后来在新华文坛大放异彩的领军人物(二者后来皆获建国以来最高荣誉之“新加坡文化奖”)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就在这一年,建裕的首部马华对照译作《印尼名诗选》由上海书局出版。
此时的南大学子学习马来文的热潮方兴未艾(始于1957年马来亚独立),精通马来文的建裕也加入了“小老师”的行列。与此同时,他还成为南大学生会主办的刊物——《大学论坛》马来文版的主要撰稿人。
在中文系就读一年之后,偏重理性思考的建裕毅然转入历史系,专属于他的理性王国之门徐徐打开,但文学从未离他而去。
边读书边当马来文小老师的建裕在云南园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翻译及整理的马来文短篇小说、诗歌及民间故事等集结成书。
1960年,他的第一部翻译小说集《印尼短篇创作选》及三部民间故事集《爪哇民间故事》《苏门答腊民间故事》《鸦佬民间故事》出版。他的首部散文集《印尼散记》及首部中篇童话译作《怪鸟之子》也在这一年出版。
1961年,他的民间故事集《马来亚的传说》及诗选集《凯里尔·安哇诗选》《马来新诗选》出版,这三部作品皆属译作(马华对照)。同年,他的评论集《马来新文学的独特性》出版。
1962年,他的译作《南苏拉威西民间故事》《爱情·眼泪·歌声》《西洋名诗选》及评论集《现阶段的印尼新文学运动》出版。
这一时期,他在撰文介绍马来及印尼文学的同时,不断有评介马来及印尼文学的论文,也有翻译改写的作品刊载于《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及《南方晚报》。优秀的印尼中篇小说《归来》(译作)也于这一时期在《南洋商报》连载,那些后来集结成册的民间故事集大多亦曾刊载于上述报章。可以说,此时的建裕扮演着马华文学和文化桥梁的角色。
1962年年底,获颁文学士学位的建裕离开了云南园。
1963年,建裕进入印尼大学文学院修读印尼历史。
应付学业之余,他也在雅加达的华文报《火炬报》兼职,并在母校巴中和日新中学教英文和印度尼西亚历史两门科目,可说是“半工半读”。1964年,他把在南大时翻译的小说《归来》重新整理出版。次年,他应出版社的要求,把早年翻译的曾在印尼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民间故事集《蛇王子》及《鼠鹿的故事》整理出版。
1965年,建裕获印尼大学颁发的历史学硕士学位。
1967年,他在机缘巧合之下赴澳洲莫那什大学研修东南亚史及西方殖民史。三年后,他获颁历史学硕士学位。也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跟一位中学同学的妹妹结为连理。之后,他应邀赴美国俄亥俄大学研究印尼华人社群问题,并于1967获颁硕士学位。次年,他前往华盛顿美利坚大学修读博士课程,三年后获取哲学博士学位。
-600x492.jpg)
青年时期的廖建裕(摄于1965年)
重返新华文坛
1975年杪,建裕回到了新加坡,受聘为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专事印尼政治、中印关系及亚细安华人研究。一年之后,他的独生女出世。
家庭及事业趋于稳定的建裕又开始经营起自己的“副业”来。事实上,回返新加坡不久,停笔八九年的他即重新开始用华文写作,重新回返新华文坛。除了在华文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及评论,他的马华翻译工作也有了新进展。
1980年,他的翻译小说《还乡》(新版《归来》)及《印尼民间故事选》(第一、第二集)相继出版。1990年,他的译作《乌士曼·阿旺诗选》出版。这是一部较完整的马来诗人的诗歌作品华文译作,该诗人在马来文坛占据重要地位。
1982年,建裕转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担任政治学高级讲师;1994年,他升任副教授;2000年,他荣升教授。2002年6月,年届耳顺的建裕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国大。
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达致巅峰。1984年,他的诗集《船民》出版;1987年,他的诗集《我不是过客》及《春天,飘落在新加坡河面》出版;1999年,他的又一部诗集《谷衣诗选》出版。
“学者诗人”,名不虚传。
为霞尚满天
离开国大之后,建裕并未停下脚步,他受聘重返东南亚研究所担任访问研究员,同时担任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至今。此外,他还曾于1998-2002年及2006-2010年两度担任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2006-2013年,他担任新加坡华裔馆馆长。成立于1982年的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是一个致力于文化历史研究与普及的学术团体,旨在推广亚洲、尤其东南亚华裔社会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成立于1995年的华裔馆则是全世界首个专门研究海外华人的大学研究中心。退休后,建裕身上的担子似乎更重,他的理性王国疆域有增无减。
虽然日理万机,但他依然笔耕不辍。2004年,他把近年来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及翻译小说汇集成册,是为《谷衣文集》。
基于对诗歌的偏好,2012年末,他即萌生了出版一部本地马来族与华族双语诗选的念头,旨在通过互相介绍本地两大族群的文学作品以促进文化交流。
2015年7月,由廖建裕主编并双向翻译的马来文与华文双语诗集《新加坡:我的城市我的家园》出版。该诗集收录了马来族、华族各15位诗人的32首诗作,主题是新加坡的国家历史与认同。
2018年,建裕的诗集《永远的南大湖》出版;2022年,他的又一部诗集《狮子城》出版;同年,他的译作《新、马、印当代马来诗坛泰斗及其作品译介》出版;2023年,他的又一部译作《凯里尔·安哇尔诗歌全集》出版。
虽已八十又三,但无论作为学者还是诗人,建裕的脚步依然匆忙且稳健。他穿行在自己的理性王国里,飞扬的诗意让他的天空充满了迷人的色彩。
适合送给他的,只有刘禹锡的千古名句了: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廖建裕近照
后记
那晚(8月28日)前往吊唁老作家张挥时碰见文友林锦,闲谈中他告诉我廖建裕值得一写。回家上网查找对方资料后托寒川代为联络,很快便敲定了采访时间。
那天早上八时许,另一半即载送我至坐落于国大边缘地带的东南亚研究院门前。距离约定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但我丝毫不敢懈怠,急急推开研究院大门落座锦鲤池边,拿起手机翻看起前一晚整理的资料来。
9点45分,匆匆而来的老教授带我步入他的办公室。11点45分,我准时离开。
虽然之前对他几近一无所知,但两个小时的采访之后,他的形象在我脑海已然鲜活而生动,这跟他思维之敏捷及思路之清晰有着直接的关联。
他的身份首先是一位学者,其文学创作尤其是译作跟他的学术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自己的创作则以诗歌为主。围绕“学者诗人”这一定位做文章之时,我的侧重点其实在他称之为“副业”的一面,加之字数有限,局限在所难免,但求不留遗憾就好。
感谢林锦!感谢寒川!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320x202.jpg)
-320x202.jpg)
-320x202.jpg)
-320x202.jpg)
-320x202.jpg)
-320x202.jpg)
-诗歌-(2008-青年书局)-320x202.jpg)
-诗歌-(2008-青年书局)-320x202.jpg)
-民间故事-童话-传说-(2009-青年书局)-320x20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