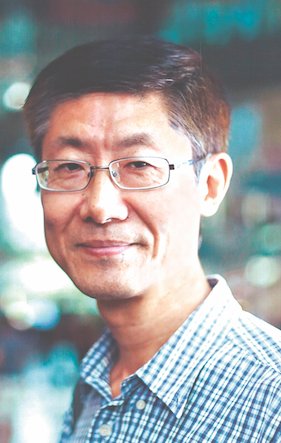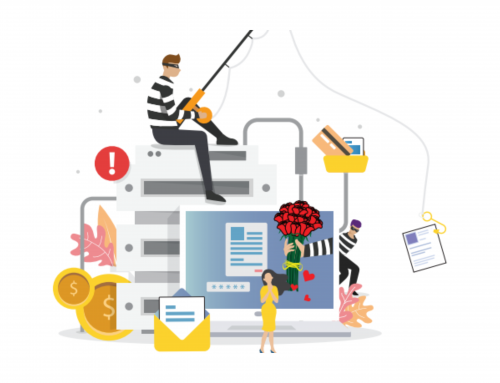一封家书的联想
章良我
退休工程师

新冠疫情笼罩下,即时通信消息漫天飞。好消息和坏消息,真相和假象,互相在争夺眼球似的。于是突然想念起互联网史前“家书抵万金”式的慢时代来。
28年前,我刚刚来新加坡,在初期的那段三个来月的光景里,与分居两地的妻子飞鸿不断,鱼雁往来。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曾经盼望期待的书信在哪里?
留下印象的只有那第一封,也就是我在新加坡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家书》中引用的那封:“送走你以后,我骑车跑了好多书店,只买到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拿回家翻开一看,哇,新加坡只有那么小小一个圈。去外地出差,特地买了一本袖珍世界地图册带在身边。每天一有空闲,便翻到有新加坡的那一页,看看新加坡。但图册上的她依然是一小块,根本找不到你住的地方。”
在社交媒体流行的当下,人人喜欢用手机照相记录自己的行程,而在以前的慢日子里,人们是用文字来记录他们各自的旅行经历的。就拿早期来访新加坡的旅者来说,其中就有这样一中一西两位写作者,给世人留下了他们当年的旅行记录。
1887年,从自己的曾祖时就世代居住于今天上海浦东新区界的李钟珏,前来新加坡游历两个月,回去后写下个人的观感,为世人留下了一本《新加坡风土记》。
比他早八年,英国人伊莎贝拉博德(Isabella L. Bird)来到新加坡,给我们留下她在东亚及东南亚游历的书信体游记读本《黄金半岛》(The Golden Chersonese)。她在1879年1月19日写于新加坡的信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译文如下:
我觉得多数热带殖民地的淑女们只活在一个“回家!”的念头里。这里的生活沉闷而漫无目的,或根本谈不上生活,有的只是生存。我在新加坡的欧洲人身上见过最具活力的景象,莫过于是妇女在赶着写信。面对任何申诉和邀请,她们的回答总是:“你知道的,今天可是寄信日。”或“我正在写信。”或“在寄信之前,我没空!”急迫的心情无法挡,即便是虚弱的英国女子也尽其所能地为“家乡的友人”奋笔疾书。从这忙乱和兴奋以及赶在最后一刻冲去邮局的举动,甚至整个社区沸腾的情况来判断,人们可能以为是因为一两年才能寄信一次,殊不知这可是每星期都会出现的景象。同样的,收到来信也是一件大事……
19世纪的英国妇女,陪伴她们的丈夫前来本地担任大小职位不等的殖民地官员,自然是远离家乡倍思亲,而写信是当时人们与远方亲人保持联络的一种世代相传的方式。不像如今廉价航空时代,世界已成为一个地球村,免费的及时通讯和社交媒体更是覆盖天涯海角,写信和读信早已是正在消失的人类传统之一。
科技虽然取代了家书,但改变不了人们更想要的相聚,以及想要回家的心。尚记得冠病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初期,新加坡政府决定敞开国门,让身在海外的国人回家避疫。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世上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自己的家园。而天下最令母亲牵挂的,便是漂泊在外、云游异乡的游子。
我的一个邻居的女儿在本地大学毕业后,去伦敦修读硕士课程。课程刚修了一半,英国便沦为疫区,她逃离了英伦,返回新加坡,又通过远程上课,最后得以完成学业。与此同时,我家中已经入读大学的长子,本来入住学校宿舍,因为疫情回到家中。原来在高年级学期时可以申请海外学府交流计划,也因突发疫情而被搁浅,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重读我的“家书”,不禁想起1993年时候的新加坡,那似乎已经是一个久远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从一个时代迈入另一个新时代的速变过程,既有让人兴奋的感觉,又有令人惋惜的感慨。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个流动的过程:在一个地方出生成长,然后离开家乡在外打拼。有人在外建立了自己的家园,有人漂泊他乡后又重返故地。也有人一生坚守出生之地,只是偶尔出外旅游,体味不同的人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