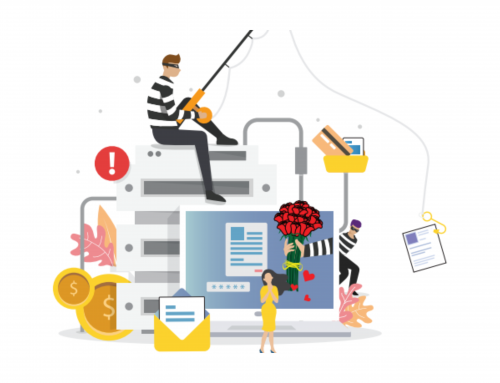读词典 逛京城 品京味儿
文·汪惠迪
图·上教社
我在新加坡从事华语文工作16年,如果有人问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新加坡人有超强的语言能力,新加坡好像一所语言学院。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有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新加坡习称淡米尔话)和英语四种。华语(Mandarin)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共同语之外,还有几种主要方言:福建话(新加坡习称,即闽南话)、福州话、潮州话、客家话、广东话、海南话。这几种语言集中在一个幅员724.4平方公里、人口564万的蕞尔城市岛国里,相互接触与碰撞,彼此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自1979年以来,新加坡一直坚持推广华语。现在,17到39岁之间的新加坡华裔年轻一代,80%能流利地讲华语了。在地球村里,“华语”一词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使用频率不断提高,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变化,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2010年5月)的“前言”和《全球华语大词典》(2016年4月)的“序”将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不过,《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第7版,2016年9月)对“华语”的解释依然是“指汉语”;《现代汉语应用规范词典》(2019年1月)的释义是“中国话,多用于境外华人对汉语的称谓”。
在客居新加坡的岁月里,我结识了好几位华语电台和电视台的主持人或播音员,也结识了好几位话剧界与相声界的朋友,他们的华语讲得都挺标准。有一次与程茂徳先生聊天儿,他一开口,我就冒昧地问他祖籍是不是北京,因为他讲的华语与众不同,带京腔,有浓郁的京味儿。程先生回答说,他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他这一口带京腔的华语全是靠模仿学来的。语音,口耳之学,靠模仿是可以习得的。
我是从香港去的新加坡,在香港工作时曾接触过好多位从北京移居香港的汉语教师,他们的普通话讲得很标准,有的就跟程茂徳先生一样,一口京腔。在香港,居然有人愿付高额学费,特请这样的老师个别教授普通话。我的一位同事是厦门人,讲得一口京腔普通话,挺受学员欢迎。这两件事儿让我看到了京腔普通话在境外和海外的市场价值。
普通话只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它不是北京话,北京话跟上海话、福建话、广东话一样是方言。我在早报工作时的同事陈伯汉先生是上世纪50年代华侨中学的学生、话剧圈的活跃分子,一口北京腔标准华语说得挺溜的,曾被北京籍的历史老师误认为同乡。
伯汉兄回忆说,1959年自治伊始,新加坡广播电台在维多利亚剧院举办综艺演出,他跟朋友曾鹏翔受邀参与其盛。演出那天,首任总理李光耀是座上嘉宾,休息时到后台跟艺人一一握手,走到曾鹏翔面前时对他说:“你的华语很好听。”当时,曾鹏翔表演的是诗歌朗诵,用的就是“北京腔标准华语”。后来,他凭那口漂亮的华语,在广播界大放异彩十几年。
伯汉兄说,当年用“北京腔”形容华语,不过是借以标榜华语的“漂亮”,为突出标准华语的魅力提供一个参照点。讲究“漂亮华语”在19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蔚然成风,在同侪中,似乎只有程茂德始终坚持北京腔,不论什么场合都不肯“放低身段”(详参陈伯汉《新加坡的标准华语》和《新加坡的漂亮华语》,2014年5月19日和6月9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拜读伯汉兄写的这两篇回忆文章后,我脑海中油然浮起一串问题:新加坡人为什么要借“北京腔”标榜华语的“漂亮”呢?为什么连李光耀都觉得曾鹏翔的北京腔华语很好听呢?程茂德先生又为什么那么执着,始终坚持北京腔,不论什么场合都不肯“放低身段”呢?我想,原因之一是北京话比普通话更生活化,更口语化,更接地气,更贴近大众。北京话的儿化音现象比普通话多,语言因而显得绵软、动听。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为躲避新冠疫情,远离群魔乱舞、暗淡失色的“东方之珠”,我一溜烟儿似的回到内地江南老家,宅在家里喝茶,读书,听听音乐,看看电视,倒也舒坦。忽一日,看到微信公众号上一则书讯:《北京话儿化词典》(增订本,以下简称“增订本”)出版。随即网购一册,次日书到,开卷阅读。
说起“读”词典,不禁怀念起新加坡华文界的前辈学者卢绍昌先生来。我与卢先生相识于香港,熟稔于新加坡,他曾对我说过,有空就读《现代汉语词典》。以前我总以为词典是供“查”的,不是拿来“读”的,退休后不忙着“揾食”,闲云野鹤似的,有的是时间,于是就学卢先生读词典了。
“增订本”收录北京话中的儿化词语7400条,“它们绝大部分还活跃在今天的口语或书面语中”,而条目所用书证都选自“充满京腔、京味儿、京韵,又京范儿十足的佳作”,并随文注明出处。从18世纪中叶清乾隆年间的《红楼梦》到2017年3月出版的《北京话》,共计77种书刊,另有“其他主要参考书目”17种,总共94种之多;其中新加坡人熟悉的老舍的著作最多,共15种。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前副所长张伯江先生在为这部词典所写的“序”中说:“北京话儿化现象的语言学价值,在这部词典丰富的实例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我读“增订本”,还深深地感受到它彰显了北京话儿化现象的文化价值。“增订本”有意增收一些体现北京民俗、风土人情、独门手艺、著名街景、景区、城池的词语,我特喜欢读这些条目。比如我们常在媒体上听到或看到“四九城儿”,只知道那是北京城的代称,不知道它的来历。“增订本”告诉我们,它泛指当年北京城的布局。旧时,北京有内城、外城之分,内城分东西南北四个城区,共有九座城门:朝阳门(齐化门)、崇文门(哈德门)、正阳门(前门)、宣武门(顺治门)、阜成门(平则门)、德胜门(健徳门)、安定门(安贞门)、东直门(崇仁门)、西直门(和义门),统称“四九城儿”。有趣儿的是每个城门各司其职,譬如正阳门走龙车(皇帝每年出此门到天坛祭天,到先农坛耕地)宣武门走囚车(犯人被押往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处斩),德胜门走兵车(出城),安定门走兵车(回城)。再如“燕京八景儿”,这是老北京著名的八处景点,即太液秋风(在中南海)、琼岛春阴(在北海公园)、蓟门烟树(在西土城)、卢沟晓月(在卢沟桥)、金台夕照(在金台路)、西山晴雪(在香山)、玉泉趵突(在玉泉山)、居庸叠翠(在居庸关)。
俏皮话儿是“指活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幽默、生动、活泼的话语”,它简洁、形象、幽默、风趣,饱含风土人情、富有生活哲理,“是人们多少年积淀下来的”,不失为我们了解北京俗文化的一个窗口儿。
北京话里的俏皮话儿十分丰富,是北京话的一大特色。限于篇幅,仅举一例说说。比如“嗝儿”,俗指死,含诙谐或不尊重意,常常是小孩儿口中说的粗俗的戏谑语。同义的还有“嗝儿踹”“嗝儿了”“嗝儿凉凉了”“嗝儿屁”及“嗝儿屁啷当”“嗝儿屁着凉”“嗝儿屁着凉大海棠”等。周有光先生就写过一篇讲“嗝儿”的语文小品。
话说中国“文革”期间,1971年9月13日,林彪连夜乘专机仓皇出逃,不料飞机失事,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上人员全部暴尸于异国荒野。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随行的一个会讲华语的记者拿着红皮袖珍本《毛泽东语录》,指着林彪的照片问一个胡同儿里的小孩儿:“他到哪里去了?”小孩儿回答说:“嗝儿了。”老外听不懂,再问:“什么?”小孩儿:“嗝儿屁了。”老外三问:“什么?”小孩儿:“嗝儿屁着凉了。”老外四问:“什么?”小孩儿:“嗝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记者十分无奈,“啊”地叹了口气,原来他始终没有听懂。当时,京城的小孩儿都知道林彪是个大坏蛋,摔死了,所以用一连串的戏谑语来回答记者的问题,谁知对牛弹琴,听得老外一头雾水,好不尴尬。他如“赔本儿赚吆喝”、“响鼓不用重槌儿”、“缩脖儿坛子”(形容身材矮小、颈项短的人)、“听蛐蛐儿叫唤去了”(借指人死了,蛐蛐儿即蟋蟀),运用了鲜活生动高超的修辞手法。像这样的俏皮话儿,“增订本”增补了不少。读这些词条,觉得挺有趣儿。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形成于公元1840-1860年间,1917年始进入鼎盛期,至今已有百多年历史了。京剧在北京扎根、生辉,深受北京人喜爱。“增订本”增收了“范儿”,这个词源于戏曲表演,原指演员在舞台上表现出的一种从容自若、信心十足、精神饱满的状态,引申为“风格、做派、气派”之意。近年来,在中国的媒体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新“范儿”,如“京范儿”“北京范儿”“中国范儿”“国际范儿”“民族范儿”“文化范儿”“文艺范儿”“时尚范儿”“君子范儿”“淑女范儿”“倍儿有范儿”等等。说得文雅一点,“范儿”就是“风范”(风度与气派)。“范儿”都蕴蓄着正能量,是个褒义词儿。
如前所述,在香港和新加坡都有人对京味儿情有独钟,“增订本”富有浓郁的“京味儿”。那究竟什么是“京味儿”?如何理解“京味儿”?这还真是个问号儿。作者告诉我们:“京味儿”不仅仅是形象、生动、丰富的北京话特有的语音、语调,也不仅仅是儿化词语,它体现的是一种有着丰富历史传承的、厚重的北京方言文化,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增订本”作者贾采珠是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从小生活在北京城,对北京话,特别是其中的儿化词比较熟悉,对研究儿化词怀有浓厚的兴趣。1990年,她编著的《北京话儿化词典》在北京出版;2019年,“增订本”在上海出版。初版和“增订本”倾注了她几十年的心血。
“增订本”一典在手,笔者想读就读,想查就查,忽前忽后,随心所欲。读着读着,浮想联翩,1958年我初到北京,那会儿正当年轻,好奇心很强。到王府井溜达,听马路上的交警、百货大楼里的售货员、饭庄里的服务员和公车上的售票员讲北京话,自觉十分过瘾。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猫在家里读词典,好似又到北京了,正在逛京城,品京味儿,瘾头儿又上来了。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