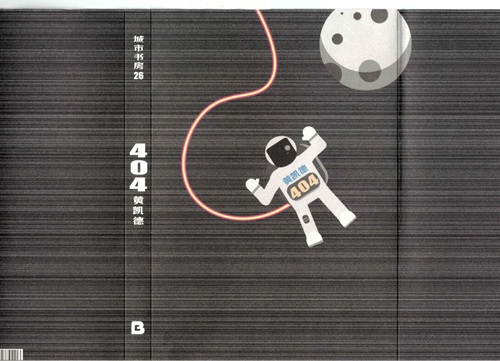班丹花园与德曼花园
——与潮汐共生 与海洋共长
文图·李国樑
.jpg)
班丹花园与德曼花园地形图(根据2025年谷歌地图绘制)
班丹蓄水池东侧是班丹河,西侧是裕廊河。在“两河流域”之间填平的沼泽地上,坐落着拥有5700多个组屋单位的班丹花园(Pandan Gardens)与德曼花园(Teban Gardens)。这里最早一批组屋于1975年破土动工,转眼间已迈入半个世纪。

班丹花园与德曼花园组屋区已经落成半个世纪
德曼花园的名字源自隐匿在裕廊河红树林间的甘榜爪哇德曼(Kampong Java Teban),班丹花园则承袭马来甘榜双溪班丹(Kampong Sungei Pandan)的脉络。这片湿地曾经是新加坡最丰饶的虾场之一,每公顷年产2500公斤海虾。直到1960年代末,这里仍可见渔夫与“虾兵蟹将”打交道的身影。
随着裕廊集团启动填海工程,这片土地的命运被改写。自1978年起,裕廊工业区员工家庭陆续迁入。这里曾汇聚阿尔法·罗密欧(Alfa Romeo)汽车、徕卡(Leica)相机、通用电气(GE)、新加坡造币厂(Singapore Mint)等国际品牌的展销室与生产线。
21世纪初落成的巴西班让综合码头(Pasir Panjang Terminals),为两百多家全球航运公司提供服务。这个取代丹戎巴葛码头的设施,预计于2040年停止运行,由正在兴建中的大士港取代。
水域记忆:从虾场到休闲水池

班丹蓄水池的前身是虾场核心区
班丹河口旧称“大港”,中游的杜佛森林因此得名“大港内”。女皇镇史德林路曾有个“无尾港村”(Boh Beh Kang),因其蜿蜒曲折、看不见尽头而得名。后来才发现它是大港的上游,流经大港内,从班丹河流入新加坡海峡。
直到新加坡独立年代,班丹河口这片肥沃的湿地仍是全岛虾场核心区。1974年筑堤成库后,虾场转型为班丹蓄水池,亦成为划艇、帆船等水上运动的乐园。
昔日班丹河口潮间带上的一道道虾池堤坝,堪称一部养虾人的微型经济史。新加坡最早的虾池出现在加冷河下游与芽笼河沿岸的滩涂地带,因兴建加冷机场而消失。日据时期,沿海渔业遭受严格管制,使得海产供应锐减。许多失业者在困境中转移目光,再度催生依赖潮汐的虾池养殖业。很快,巴西班让至裕廊河一带的沼泽地区都被改造成虾池;日军甚至征用其中一些池塘,试验养殖源自非洲的罗非鱼(俗称“日本鱼”或“尼罗红”)。二战后,虾池业持续繁荣,养殖版图拓展至实龙岗河与实里达河沿岸,以及乌敏岛与德光岛。
沈国栋就是在班丹河口养虾长大的。他家的虾池构造与其他的大致相同:工匠们在沼泽区堆筑梯形土堤,顶部宽约一米,基部宽五米,围合成咸水养殖场。关键的水闸系统暗藏玄机:涨潮时提起铁丝闸网引入海虾;退潮时落下闸网防止虾群逃逸。池两端另设活动闸门,利用潮汐来换水。
海虾昼伏夜出,日间藏在池底,黑夜才浮上水面,因此催生了独特的捕捞方式。渔家等待夜幕降临后,往池中注水;待虾群浮游时,关闭一端闸门,在另一端张网截流,潮退时把鱼虾一网打尽。
日常管理方面,每两三个月必须清除随潮水入侵的杂鱼水蛇等,以保障虾群健康生长。池主让附近的马来甘榜居民进入虾池捞鱼,但严格规定不准捕虾。互惠互利的不成文条规,既维系着睦邻关系,也守护了养殖收益。时光留不住这段在海岛边缘依赖潮汐律动、与海共生的养殖史,不过可以通过文字留下记忆。
信仰地标:哈萨纳回教堂
承载着外岛居民的迁徙记忆.jpg)
哈萨纳回教堂(Masjid-Hasanah)承载着外岛居民的迁徙记忆
宗教也在变化的格局中找到立足之地。1971年落成的哈萨纳回教堂(Masjid Hasanah),承载着外岛居民的迁徙记忆。
世代居住在裕廊一带外岛的约1万名马来居民,因工业发展搬迁至本岛。由于最靠近的巴西班让回教堂路途有些偏远,裕廊镇管理局特别为原外岛居民兴建了这座回教堂,设施比外岛上的祷告室完善得多。
此后,哈萨纳回教堂历经火灾与重建,信徒也从岛屿社区扩大到附近的新住户。如今宏伟的哈萨纳回教堂是于2025年扩建落成的。
无痛死亡:猪只屠宰场
猪肉占据本地肉类市场的三分之一,人均年消费量约20公斤。1980年代,新加坡全面淘汰养猪业,我们也失去了世界上最先进、最密集的养猪场。生猪与冷藏猪肉改由外国进口,主要来源地包括砂拉越及马来西亚其他地区、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巴西和西班牙等。
位于裕廊布罗巷(Buroh Lane)的Primary Industries屠宰场,每日处理400多头砂拉越生猪。其现代化屠宰流程严格,必须遵循新加坡食品局(SFA)的安全与卫生标准,确保食品供应的安全性;此外必须贯彻人道主义,让牲畜无痛死亡。新式屠宰业的精密流程,以及二氧化碳致昏、低温处理等工序,与昔日依赖潮汐节奏的虾池业,形成鲜明的对照。
绿色能源:乌鲁班丹供水回收厂

在国家环境局的安排下,笔者参观乌鲁班丹供水回收厂,背景是鸡蛋型沼气罐
旧笃德路(Old Toh Tuck Road)有个特别的鸡蛋型沼气罐(digester)地标,那是于新加坡自治时期落成的乌鲁班丹供水回收厂(Ulu Pandan Water Reclamation Plant)。沼气罐也是一座科技展示场,让公众了解利用生物分解技术将固体残渣转化为绿色能源的过程。
公用事业局(PUB)的Water Hub建在供水回收厂旁,让我们较完整地了解在地底下进行的自动化污水回收作业。以住家为例,厕所、冲凉房、水盆等污水残渣经过笔直的大水管,流到地底深处的下水道,再输送到各个回收厂。全岛公共下水道全长3600公里,地面上有10万个窨井,让工人进行检查、疏通和维保。

乌鲁班丹供水回收厂于1960年代落成时,这一带地势荒芜,渺无人烟
21世纪初,全岛启动的另一项大工程是深隧道阴沟系统(Deep Tunnel Sewerage System)。地底深处48公里长的“霸级”阴沟已经完工,另外的40公里正在兴建中。这些阴沟的水管直径超过3个人的高度,将污水输往乌鲁班丹、樟宜、克兰芝和即将完工的大士供水回收厂。当大士供水回收厂与新生水厂落成后,运作超过60年的乌鲁班丹供水回收厂将功成身退。
下水道最常遇见的问题是管道堵塞。人们通常误以为这是由粪便和厕纸导致的,其实不然,因为这些物质可在水中分解。通常引起堵塞的是诸如厨房纸、擦脸擦嘴的纸巾、湿纸巾、卫生棉、抹布、汤汁、食用油以及硬化油脂等。大家或许对纸巾也会造成管道堵塞感到意外,那是因为纸巾比厕纸密实,在水中难以分解的缘故。
我们每个月定期收到的水电账单,其中“Water Services by Public Utilities Board”所涵盖的费用包括污水处理。所以,为环保尽一份力,也等于让自己的荷包好过一些。
供水回收厂旁的吉宝西格斯新生水厂(Keppel Seghers Ulu Pandan NEWater Plant),原为集水区,在暴雨期间将多余的雨水排入大海。如今的新生水厂将处理后的污水进行过滤和消毒,部分用于工业冷却用途,部分注入蓄水池。
乌鲁班丹焚化厂:新加坡第一座垃圾焚化厂
1979年启用的乌鲁班丹焚化厂(Ulu Pandan Incineration Plant)是东南亚首座垃圾焚化厂,曾经是供水回收厂的近邻。由于垃圾填埋场空间有限,新加坡独立期间已规划采用焚化方式处理垃圾,并利用焚化热能发电。如今焚化能源占全国总电力供应的2%。
这一带曾经是荒芜之地,周边5公里内没有住家。随着住宅区扩展至焚化厂周边,垃圾车与供水厂的异味时常引起居民投诉。这座焚化厂在运行30年后正式关闭,原址变成一片绿地,垃圾车的气味已成追忆。
与海共生,以海作乐:班丹河畔的“航海史”

新加坡游艇俱乐部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游艇俱乐部之一
1826年,包括新加坡、槟城与马六甲的海峡殖民地成立,新加坡帆船俱乐部(Singapore Yacht Club)随之诞生,后来更名为新加坡皇家帆船俱乐部(Royal Singapore Yacht Club),新加坡独立后再次改名为新加坡游艇俱乐部(Republic of Singapore Yacht Club)。它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游艇俱乐部。
新加坡游艇俱乐部经历过解散与重生,曾经在南部港湾和圣淘沙落户,千禧年前于班丹河畔现址落户。俱乐部码头已成为本地航海爱好者的游艇停泊处。

班丹河畔的造修船厂提供船舶维修、可再生能源、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造与支援
1960年代末,班丹河畔陆续成立多家造修船厂,提供船舶维修、可再生能源、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造与支援。虽然新加坡被誉为一流的海运城市,然而造修船业一度被视为夕阳工业,业者多管齐下并引入现代化科技,终于让该行业生存下来。
为来往商船供应物资和备件,是新加坡发展成为国际海事中心的关键周边行业之一。例如本茱鲁驳船码头(Penjuru Lighter Terminal)每年有7万艘驳船停靠,处理的货流量约80万吨,就像昔日来往新加坡河与轮船间的木船一样,是一股海事物流的经济力量。
坚持工艺,追求艺术:新加坡造币厂
.jpg)
NS55纪念章(图源:Singapore-Mint)
新加坡独立后成立新加坡造币厂(Singapore Mint),铸造本地流通硬币。不过,如今我们已不再大规模生产货币,而是专注于为本地及国际市场制造精美的纪念币、纪念章、书签和磁铁等收藏品,客户来自文莱、不丹、柬埔寨和澳门等。
在本地市场中,农历新年的生肖纪念币系列深受欢迎。其中牛年纪念币以科尼岛为主题,巧妙地融入一段传说:科尼岛刚和本岛衔接完工开放时,岛上曾出现过一头黄牛。设计师将这故事镌刻于币面,使纪念币更具本土特色。
近年来,造币厂推出具象征意义的纪念章,例如特朗普与金正恩峰会,以及新加坡国民服役55周年(NS55)等。NS55纪念章的设计刻画海陆空三军、民防部队及警察部队的五名制服人员,生动地记录了国民服役制度的历史。最新推出的“鑫狮金条”以威武雄狮为设计图案,为消费者提供多一项投资选择。
造币厂的核心在于一支技艺精湛的工匠团队。尽管现代机器可以雕刻出人像的基本轮廓,但要赋予作品生动的细节,如面部表情、眼神中的光彩、动物毛发的纹理,甚至微妙的笑纹,仍需匠人精雕细琢。经验丰富的工匠大师们通过纯熟的技艺,使纪念币更具艺术价值。
正是这份对工艺的坚持与对艺术的追求,使他们巧妙地融合科技、手工技艺与艺术。从概念设计到三维建模,再到打造能承受高压的模具和操作机器,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完美。这一切皆发生在德曼花园一栋低调不起眼的建筑中。
班丹花园与德曼花园交织着从潮汐虾池和马来甘榜,进入水源、工业、海事和环保作业的发展历程,承载着独特的“与潮汐共生,与海洋共长”的篇章,续写着国人的生命华章和坚韧气质。
参考文献:
[1]陈明顺,“新加坡虾池业”,《南洋文摘》1963年第7期。
[2]陈映蓁,“德曼花园两河之间的变与不变”,《联合早报》2023年12月3日。
[3]“你不曾了解的新加坡造币厂”,《联合早报》2021年1月24日,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896203921153286, accessed on 31 March 2025.
[4]沈国栋口述记忆,2022年6月4日。
[5]Bhaskaran Kunju and Kevin Seet,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Yacht Club,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s://www.nlb.gov.sg/main/article-detail?cmsuuid=53e51d2a-a8e4-41bd-875a-bf29c40753b1, accessed on 27 March 2025.
[6]Jenni Marsh, Forgotten Singapore: evicted islanders grieve for lost ‘paradis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updated 30 June 2016. https://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article/1805255/forgotten-singapore-evicted-islanders-grieve-lost-paradise?module=perpetual_scroll_0&pgtype=article, accessed on 22 September 2025.
[7]Jurong Port, https://www.jp.com.sg/, accessed on 25 August 2025.
[8]Masjid Hasanah, https://www.hasanahmosque.sg/, accessed on 22 September 2025.
[9]Pandan Reservoir, https://www.roots.gov.sg/places/places-landing/Places/landmarks/jurong-heritage-trail/pandan-reservoir, accessed on 27 March 2025.
[10]The Singapore Mint, https://www.singaporemint.com/,accessed on 31 March 2025.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Pandan Gardens and Teban Gardens: Living with the Tides, Growing with the Sea
Pandan Gardens and Teban Gardens are located on land once characterised by mangroves, prawn farms and Malay villages. Nestled between the Pandan and Jurong Rivers, the swamp was restored in the 1970s and transformed into housing estates with more than 5,700 flats. By 1978, many workers in Jurong and nearby factories had relocated their families to the new communities.
The names themselves resonate with history: Teban Gardens derives from Kampong Java Teban, whereas Pandan Gardens traces its roots to Kampong Sungei Pandan. These connections preserve memories of seafaring communities before the landscape succumbed to modernisation.
Prior to reclamation, this coastal region was one of Singapore’s most prosperous prawn farming zones, producing 2,500 kilograms per hectare annually. Prawn farms and ingenious tidal management systems once prevailed in the wetlands. Farmers constructed trapezoidal embankments featuring sluice gates to allow seawater and prawns to enter at high tide, while capturing them during low tide. Prawns surfaced at night for harvesting.
Local kampong residents often fished in the ponds under unspoken rules that safeguarded the core prawn revenue. This tide-dependent economy garnered momentum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hen coastal fishing was under strict control, and expanded across rivers and islands after the war. By the 1970s, however, the farms were gone and were replaced by Pandan Reservoir. The reservoir represents the conclusion of an era when livelihoods literally followed the rhythm of the sea.
Religion also established a presence in this evolving landscape. The Hasanah Mosque was initially intended for Malay families resettled from neighbouring islands. The new mosque expanded alongside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y. In 2025, a larger building was unveiled.
Up until the late 1980s, pig farming was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to the local diet. With the elimination of pig farming for environmental and other reasons, the contemporary slaughterhouse on Buroh Lane replaced backyard farms. The facility handles hundreds of imported pigs daily, adhering to stringent hygiene and “humane death” standards, demonstrating how technology transformed a conventional food suppl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s equally important. The Ulu Pandan Water Reclamation Plant, featuring its unique egg-shaped digester tanks, exemplifies contemporary sewage treatment and energy recovery. Household wastewater flows through underground pipes to the plant, where organic materials are decomposed into biogas. Its work is enhanced by NEWater plants that repurpose treated wastewater for industrial and reservoir usage.
Close to the water reclamation plant was Singapore’s first incineration plant. The facility began operations in 1979, pioneering waste-to-energy innovation. Despite shutting down after three decades, its existence represented an important move in tackling the island’s limited landfill capacity.
The maritime thread also runs deep.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Yacht Club is among the oldest in Asia, serving as a hub for local sailing and yachting. Alongside it, shipyards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1960s have bolstered the offshore energy and maritime sectors. The Penjuru Lighter Terminal handles tens of thousands of lighters annually, underscoring Singapore’s enduring reliance on maritime logistics. In many ways, these endeavours resonate with the prawn ponds of the past: enterprises influenced by tides, currents, and the sea’s economic draw.
Teban Gardens houses a more tranquil yet equally symbolic institution, the Singapore Mint. Established post-independence to create national currency, it now focuses on commemorative items for both local and global markets. Its zodiac coins and unique medallions for Lunar New Year, including those commemorating the Trump–Kim summit and NS55, illustrate the blend of artistry and craftsmanship with national narratives. Talented engravers infuse intricate emotions, details, and narratives into metal, safeguarding creativity and talent in an age of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The intertwined histories of Pandan and Teban Gardens illustrate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s west. The sea is not just a setting; it has shaped ways of life and created a vibrant record of resilience and transformation.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