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之光
——梁明广专访
文 · 齐亚蓉 图 · 受访者提供

梁明广
久远的故事
1929年5月24日上午10时许(农历己巳年己巳月己巳日己巳时),海南琼海牛宿坡村,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他瘦瘦小小,但哭声震天。“梁家有后了!”育有两个女儿的父亲梁文质面露喜色,母亲陈西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父亲给儿子取名明广。明广百日之后,人到中年的梁文质即告别妻子儿女南下新加坡谋生。丈夫离开后,抚养明广长大成人似乎成了母亲唯一的寄托。自明广会走路之后,她的双眼总是盯着儿子的双脚。“短命啊!短命啊!怎么脚跟总不着地呢?要改啊!要改啊!”她不断地叹息,不断地唠叨着。
1935年,母亲带着六岁的儿子自海口乘船南下新加坡跟丈夫团聚,两个女儿则留在了海南。
文学启蒙
母亲把明广带到狮城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算命先生为儿子算命,得知儿子能活到79岁时,做母亲的总算放下心来。那时他们一家三口租住在今书城角头维多利亚旅店斜对面一间店屋的二楼。明广的父亲任职于一家汇款公司,他赚钱不是很多,但养家糊口倒也不成问题。
1936年,七岁的明广入读住家附近的中华公学。虽然不曾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学前教育,但明广喜爱上学读书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不错,华文尤其突出。小明广吃过晚餐后,总喜欢跑去楼下听一位叔叔说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大半从这位叔叔嘴里听来。直到今天,他还记得叔叔告诉他,写作文要像讲故事一样。这应该是他最初的文学启蒙。
小学高年级时,明广开始大量接触《南洋商报》之类的现代读物,文学创作的种子在他的心头悄然萌发。后来得知一位老师的丈夫供职《南洋商报》时,他的心头仿佛开了一扇亮窗(多年之后,这位叫做薛残白的文学前辈成了明广的同事)。
除了博览群书,此时的明广也开始用手中的笔描画起自己的文学梦来。
但小学刚一毕业,文学少年梁明广的美梦即被日本人的枪炮声打断,后来的三年零八个月里,他只好跟随父母逃去杨厝港亲戚家避难。
投稿《南洋商报》
抗战胜利后的次年,明广入读公教中学。此时他们一家已搬至奎因街三马路,学校跟他家之间仅仅隔着一个联络所。
父母对于明广的学业从不过问,事实上,性格独立的明广根本无需他们操心。课余时间里,除了学校图书馆,他也是友谊书局及长河书局的常客,书局老板跟这位喜爱读书的小弟弟早已成了老熟人。“好好读书,长大后一定有出息。”他们常常这样对他说。
大量阅读使得明广的语文根底愈加深厚,眼界愈加开阔,写作能力也远远超越同龄人。时任校长姚国华的哥哥姚任父一直担任明广的华文老师,他让作文写得顶呱呱的明广负责办壁报,虽然只是收集整理同学们的习作并贴在壁报栏里,但对明广来说,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鼓励。
刚一进入中学,明广即以完颜藉(“藉”同“借”)、黎骚、矛修等为笔名投稿《南洋商报》“商余”版。他的诗歌、散文、杂谈及影评深受时任副刊主编彭松涛的赏识,作家梦对他来说似乎不再遥远。
此时的明广已不再伸手向父母要钱,他的稿费足够自己零花及缴交学费了。
入职报馆
1950年,明广高中毕业,次年,正在求职的他得知《南洋商报》的姊妹报——《南方晚报》正在招聘记者,欣然前往报名参加考试。
一个月后,《南洋商报》本坡新闻版编辑张匡人先生及马来西亚新闻版编辑石光华先生专程前来明广家报喜,并要他在一个月后前往报馆报到。
成为《南方晚报》见习记者后的一个星期,明广接到第一份差事:采访一个青年跳楼自杀的新闻。后来,他用一首题为《故事》的诗作完成了该新闻报道。这种别具一格的新闻报道形式为他的职业生涯开启了甚为精彩的一笔,也展示了青年梁明广的与众不同。
五年之后,由《南方晚报》转入《南洋商报》做电讯翻译及国际新闻版主编的明广听闻南洋大学开课在即,突然萌生了入大学深造的念头。而此时的他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若贸然辞工,即使考入南大,学费也没有着落。两难之下,明广只好硬着头皮前往乌节路拜见素未谋面的《南洋商报》老板李玉荣(李先生同时也是意大利汽车飞霞在新加坡的总代理,他的车行位于乌节路),当李玉荣听明广说想要保留报馆的工作,同时入南大深造之时,他称赞明广有志气,不但答应让他半工半读,还让他到自己的车厂分期付款(免息)购一辆飞霞汽车代步。
后来,明广通过了入学考试,被南洋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录取,他驾着自己的新车,白天载着四位同学(分摊车油费)去南大上课,晚上到报馆做夜班编辑。此外,他还兼任星华公学的华文老师。
就这样,身兼二职又要兼顾学业的明广以全新的姿态踏入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
推动现代主义文学运动
明广入南大攻读的是欧美文学,并非华文文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有牢固的华文基础,英文则相对薄弱,是需要加强的环节。在南大接触到的欧美文学在他心中埋下了现代主义的种子,成为他日后推动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奠基石。

梁明广毕业照
大学毕业后,明广继续负责《南洋商报》国际新闻版,同时醉心于文学创作。1967年,《南洋商报》副刊编辑杨守默(杏影)病逝,他主编的《青年文艺》由偏爱文学的明广接手(兼差),明广将《青年文艺》易名为《文艺》,并在创刊日(1967年2月8日)发表《文艺版的二不主义》,提出不分地域、不分阶层征集优秀文学作品的主张。1968年1月1日,他在《南洋商报·新年特刊》发表长文《一九六八年第一声鸡啼的时候》,表示旧文艺手法已不足以描述时代与个人内心复杂的情感,鼓励写作者寻找新的表现方式,大力推进现代主义文学风潮。
新年的第一声鸡啼,激起了强烈的回响,《文艺》成为最多本地作家发表试验性作品的园地,陈瑞献、南子、英培安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受到力捧。一向不喜跟其他写作者结交的明广也跟他们有了往来,尤其跟陈瑞献成了莫逆之交。
1971年,梁明广与陈瑞献联手在《南洋商报》主编《文丛》版,大量转载国外优秀作品,同时也接受投稿,内容涉及政治及文学,注重趣味性,颇受读者欢迎。1978至1983年,梁明广主编了《咖啡座》,内容涉及笑话及闲谈,活泼生动的风格令读者耳目一新。
1983年,《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之后,梁明广在《联合早报》“言论”版及“四方八面”版开设了专栏《笑谈天下》及《胡文乱墨》。前者为政论,后者为杂谈,这两个专栏使得他的现代主义文风得以尽情挥洒。
1992年,年逾花甲的梁明广离开了报馆,他的专栏也随之叫停。
梁明广文集
七八年前的某一日,《新明日报》总编辑潘正镭问创意圈出版社总编辑方桂香是否有梁明广的代表作《填鸭》,他要送台湾学者朋友作研究之用。《填鸭》是1972年陈瑞献为梁明广选编设计出版的文集,列入陈瑞献主编的《蕉风文丛4》。
方桂香回说她只有2003年为梁明广编辑出版的《文字杂耍》,且仅剩几本样书存档。潘转而问梁是否存有此书,梁的答案是否定的。潘后来也发现国家图书馆“陈瑞献藏室”里的《填鸭》也仅剩一本。
自青年时期起即受梁明广赏识的陈瑞献得知此事后,请潘正镭协助,把梁明广当年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及“言论”版的专栏文章尽数找出来。校审过后,又托方桂香把这些文章连同绝版的《填鸭》以及《文字杂耍》以外的零散篇章汇集成专集出版。除了承担所有的费用,封面设计也由陈瑞献亲自操刀。

梁明广文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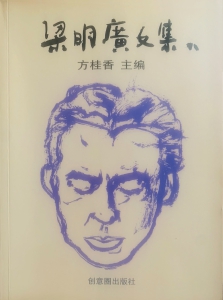
梁明广文集二

梁明广《文字杂耍》
2017年9月,一套三册的《梁明广文集》问世:《梁明广文集1》保留《填鸭》原貌,卷末另收三篇短序;《梁明广文集2》与《梁明广文集3》收录了《文字杂耍》之外的所有篇章。
总计1052页的《梁明广文集》,加上之前出版的《文字杂耍》,梁明广所有发表过的文章得以完善存留。
天时地利人和,老报人再无遗憾。
淡出文坛
自1992年退休之后,梁明广很快便淡出了文坛,名利地位对他来说成了过眼云烟。
“退了就是退了。”无执念,不恋栈。喝茶、聊天、健身、卡拉OK,饥来吃饭困来眠。
他还是会常常想起那位说书的叔叔。虽然自认讲故事的功夫不到家,但他相信这个真实的故事定能世代流传。他也常常想起母亲找人给自己算命的事,批书上的79早已成了过去,很快也就能摸到97了。“老而不死是为贼”,他笑了,淡淡地笑了。
洒脱而通透,温润且恒久。
“古玉之光”,陈瑞献说的。
后记
三年前的某个周末,受秦淮夫妻之邀,跟另一半一起参加了一个饭局。席间听到梁明广三个字,另一半双目放光,附在我的耳边说他在早报言论版读过对方的政论,写得好极了。饭毕,他撺掇我过去打招呼并要求采访,还替我要了对方的电话号码存在自己的手机里。
“梁老先生的年纪很大了,你得抓紧时间。”另一半不时念叨一下,但我终是没胆量直接打电话过去。直至完成别人帮忙联系好的几位老作家的专访,才发现梁老先生的手机号码在另一半的旧手机里,而那部旧手机因屏幕毁坏已不知丢去了哪里。
于是只好请寒川帮忙,一番好事多磨后,终于在一个阴雨霏霏的星期日近傍晚时分,走进了94高龄的老作家的厅堂。
老人家听力退化,但头脑灵光,采访还算顺利。准备离开时,他拿出四本书供我参阅,其一是1972年版的《填鸭》,其实只是夹在一起的一叠复印件,泛黄的封面锈迹斑斑,让人想起“故纸堆”三个字。另外三本分别是2003年版的《文字杂耍》及2017年版的《梁明广文集》1和2(缺3),没办法,这就是他手头的全部。
后来的两三天里,梁明广那件“高古素雕大璧”忽而触我心弦,忽而入我梦间,那四溢的色浆斑斓了我的天空。
他长寿的秘诀,或许就藏在那大璧里。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2-scaled-500x383.jpg)
与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成员合影(图源:王曾善收藏,取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Digital-Gems)-2-500x383.jpg)
-1-500x38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