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与自学成家的苏启祯
文图 · 郭永秀
2018年11月9日早上,我在新加坡大会堂聆听了《阿德下南洋》音乐会之五:《甘榜重游》。这场由郭勇德指挥的音乐会,有一首令我回味的乐曲——《甘榜趣事:阿李与阿利》(苏启祯作曲、李崇望配器)。该曲原版是口琴曲,采取马来民歌以及中国民歌《一根扁担》的音调改写而成。配合银幕上黄惠玲的皮影戏,突出了乡村生活中人们的包容、开阔、共融和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甘榜精神。
这首曲曾经在作曲家协会的音乐会上发表过,作曲者就是学者、教育工作者及作曲家苏启祯博士。不久前的一个午后,我到苏博士府上专访,他因跌倒入院,脚伤未痊愈,走动时还需借助轮椅。
谈起音乐的启蒙,苏启祯记忆犹新。他1934年出生,幼儿园时在全班前面唱歌,因为唱得好,老师给了两块动物形状的饼干作为奖励。5岁那年,他早上常在苏氏公会(242 Telok Ayer)的二楼后面玩耍,有位小提琴家住在那里,他的演奏使苏启祯着迷。另一让他着迷的乐器是踏板风琴。这是一种中国造的小型键盘乐器,演奏者以脚踩踏板,同时手指按着键盘而发音。邻家一个女孩在演奏时,交叉前臂弹奏的优雅姿态,也使他心迷神往。这一点一滴的印象,凑成了他对音乐的迷恋。
以口琴奏响音乐人生
早年的新加坡,没有音乐学院,家中不富裕的人也没有机会出国留学。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会想到以艺术作为职业,音乐只能当成是一种娱乐。但是偏偏就有些人对音乐非常着迷、非常执着,虽然是业余活动,仍然不遗余力地学习和求索,苏启祯就是这样的人。

苏启祯一开始就自学口琴,他先与我分享口琴的演奏、作曲方面的经验,从他在金炎路中正中学分校念初二时说起。
上世纪40年代末期,他参加了口琴班,指导老师是黄大信,一位来自天主教会办的公教中学的高中生。黄老师教了他们一些流行的经典曲目,如伊凡诺维奇的《多瑙河之波》和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
在那人人都不富裕的年代,口琴是最便宜的乐器了。那时每首乐曲都以C调演奏,因为用的都是C调口琴,其他调性的口琴大家都买不起,乐谱也用简谱。C调口琴只能演奏7个音,碰到半音阶就无能为力,莫说转调了。后来口琴队里有人把C调口琴的簧片刮去小部分,改变其音高,成为高半音的C#,逐个刮就变成了一把C#调的口琴了。将C#调口琴放在C调口琴上方,必要时在它们之间切换,就可以吹出所有的半音。
随着口琴队的进步,“圆号口琴”开始被引入乐队。其实它只是一个金属管,有一个狭缝,可以插入口琴,把声音放大,使它发出了像喇叭一样的金属声。不久以后,学校给了一些钱,他们买了一把能够演奏和弦的口琴,大约半米长。后来,又得到一把低音口琴,声音低沉而醇厚。有了这三种特殊的口琴,乐队演奏的效果听起来就比较完整和平衡得多了。
我们知道普通口琴是以大调设计的,其实还有一种小调口琴。就是把C调口琴的第三和第六个音降低半音。这样一来小三和弦就可以代替大三和弦。不久以后,一些同学开始尝试演奏半音阶口琴。这是一把特制的口琴,一端有一个按钮,只要手指一按,C音就变为C#音了,就像钢琴上的白键和黑键,可以自由地演奏音阶里的12个半音了。但由于每个音符只有一个簧片(复音口琴每个音有上下两个簧片),所以声音比较弱,演奏时需要加上麦克风。半音阶口琴使口琴的演奏范围扩大了,可以自由地演奏小提琴曲,只不过音域还是没有小提琴那么宽广。
多渠道的音乐自学
苏启祯说,他的音乐之旅是漫长、曲折和不稳定的。他从老师和朋友那里学习,也通过书本、电台、朋友、音乐会等自学。后来他开始了音乐创作,这磨练了他的耐心和能力,丰富了他对音乐作品的理解。
苏启祯经常与梁荣平和李煜传合作,创作音乐、演奏音乐。他曾受教于前辈音乐家丁祝三。在师资训练学院任教期间,曾参加校长保罗·阿比谢甘纳登的新加坡室内乐团演奏。他也向吴文英和当年新加坡交响乐团的中提琴主奏Mr. Basafra学习小提琴。
上世纪70年代,苏启祯协助李煜传为当时的工商小学校友会组织了一个小型小提琴组,后来扩大成一个由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和巴松管组成的室内乐团。他们在Jalan Gajus的家里排练,也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奏莫扎特的作品和本地创作。例如:李煜传的《麦里芝蓄水池》和他自己的作品《阿李与阿利》以及《掀起你的盖头来》变奏曲。
提起《阿李和阿利》,苏启祯有些兴奋,因为这是他最为人所称道的作品。这首组曲共分4段:以“甘榜景象”开始,描绘一个种族和谐共处的村庄。旋律具有典型的马来风味,节奏灵感来自马来游行鼓;接下来是根据中国民歌《一根扁担》改编成的乐段,这是收集旧货的阿李(华族)出场表演时的音乐;然后是“顽皮的孩子”,一个马来男孩和一个华族男孩快乐地打石弹子,这部分乐曲是典型的古典风格;最后是阿利(马来族)的妻子踩到一块碎玻璃,阿李帮忙止血包扎,让阿利误会,解释清楚之后,阿李和阿利跳起了和解之舞。最后这个乐章是用现代和声风格写的,因为当时苏博士对巴托克的钢琴作品非常着迷。
随后这首《阿李和阿利》由Ahmad Jaffa指挥新加坡广播电台大乐团演奏。几年后又被移植成为华乐,由郑朝吉指挥狮城华乐队演奏,再后来由郭勇德指挥新加坡鼎艺团演奏。1997年,该组曲被新加坡作曲家协会带去北京,在北京音乐厅《新加坡之夜》音乐会上表演。
苏启祯说:“念初中时对音乐创作产生了兴趣,开始尝试用唐诗做歌词,创作简单的歌曲。有规则的四句结构较易谱曲,简单的起、承、转、合方式,只需要把诗歌的情绪转换成旋律就行了。我写的第一首歌是《春天的早晨》,其实就是孟浩然的《春晓》,使用五声音阶。它描绘了诗人在一个寒冷的春天早晨醒来,听到鸟儿啁啾,感叹花的短暂生命的心情。我因为没有受过正式的作曲训练,所以读了很多关于和声、对位法和配器的书。但我觉得还是需要向其他音乐家学习,所以我写完了一首曲后,就把草稿请当时在中正中学教音乐的丁祝三先生、好友梁荣平和李煜传指正。他们都定期在音乐会上指挥合唱团,发表我的合唱和独唱作品。听众很喜欢的节目之一是《姑娘要出嫁了!》,这是一出在那几年里经常上演的乡村小喜剧,”

上世纪80年代,苏启桢在家里弹琴自怡
80年代以后苏启祯仍然继续创作。他比较喜欢的一首创作是由三首歌曲组成的组歌,那是他在中正中学的回忆。歌词来自一本诗集,讲述了中正中学的中正湖不同时段的美景,歌词取自诗人曾泓的诗。在这些歌曲中,他自由地使用了五声音阶的旋律与和声,同时运用了20世纪的现代作曲技巧。
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歌手和观众最喜欢的是独唱曲《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歌词取材于泰戈尔的《新月集》,创作曲风和灵感则来自勃拉姆斯的小夜曲。苏博士对自己的风格是有要求的。有一次他发表了一个作品,有人写了乐评,说他的作品很好听,像北欧作曲家格里戈的作品。他听了反而不高兴,作品像别人的有什么了不起,就把乐谱撕掉了。

苏启祯刊登的论文及出版的专著
除了作曲,苏启祯也尝试写音乐评论,他用的笔名是“迪安”。从中学时代开始,他为当时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和《南方晚报》写稿,为读者提供了一些讯息,如:如何欣赏古典音乐?在参加音乐会时应如何表现?作曲家如何进行创作?也有著名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如:圣桑的《天鹅》、马思涅的《沉思录》、舒伯特的《百灵鸟》等,还有一些交响诗和交响小品。后来,他出版了一本有关音乐的书,取名为《随想曲》,由当时的教育出版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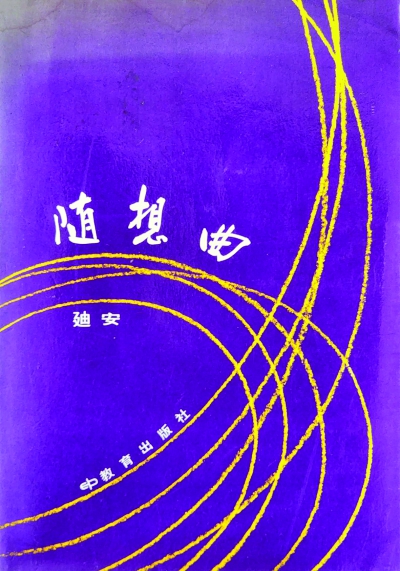
随想曲曲谱
另一方面,苏启祯也为电台定期写有关于音乐的知识,以供广播之用。这个机会促使他大量研究作曲家的作品、生平及他们的写作背景;他在听他们的音乐的同时,也阅读他们的乐谱,无形中给他很好的听觉和读谱训练。也许,这是一种更彻底的享受和欣赏古典音乐的方式。这个广播系列持续了大约两年,使他对音乐及音乐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也增进了他的音乐知识。
苏启祯认为:近年听过一场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作曲家的作品发表会,发觉马来西亚的作曲家写的作品写得很不错,技巧上比新加坡更为“现代”。不过很多音乐其实已经变成“音响”,发出一些非传统的“乐声”。他认为年轻人表现新的作曲技巧没错,但切勿走入牛角尖。因为一般听众想听的还是有旋律的音乐。那些没旋律、用尽各种不协和弦、刻意破坏节奏的“音乐”不可能成为主流。就像西方音乐一样,尽管现代音乐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但听众仍然喜爱传统的交响乐和歌剧。
至于现代华乐,苏启祯认为其困境是:若全面“现代化”,专门制造“音响”,缺乏民族色彩,那听众将越来越少。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西乐会做得更好,而“传统式”的华乐在音响上听起来又千篇一律,听不出是谁的作品。不像西洋音乐,一听就知道是莫扎特、贝多芬、布蓝姆斯或柴可夫斯基……假如现代音乐能和传统音乐有机结合,在必要的时候才出现,例如作为某种情绪或场景的描写方式,同时又具有民族色彩,那将会是很有吸引力的作品。
教育研究方面的治学
苏启祯提起他治学的过程:在念完高中以后,家里没有能力供他念大学,便申请进入当时的师资训练学院,成为一名受训教师,因为受训教师有生活津贴。毕业后他在一间小学教书,后来进入师训学院,成为一名初级讲师。过了几年,他申请到British Council的奖学金,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留学,攻读教育高级文凭(教育心理学),拿到了diploma文凭,回新加坡两年之后,又再次申请奖学金到曼彻斯特大学攻读教育学,获得硕士学位。
回新加坡以后,苏启祯继续到新加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作为新加坡大学的硕士导师,曾在教育学院任教。退休后,由当年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许通美教授推荐,转任南洋艺术学院院长。三年后,他又回到教育学院兼职任教,直到十年后才“退休”。退休后,苏启祯受前院长陈之权博士之邀,担任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研究顾问,负责训练研究人员从事量化研究,直到现在。教研中心通过提供优质的培训课程,提升我国教师的教学素养、教学能力与专业水平,并尽力促进华族语言文化在新加坡的发展。
在教育界几十年,苏启祯感觉到新加坡的教育系统的确有它的优点,但也有缺点。他认为现代人太过功利主义,有利益大家抢,没有利益就不干,这也是造成华文在本地没落的原因之一。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一次有关华文教学的争论:可以用英文来教华文吗?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苏博士却认为这其实是可以实行的方法之一。因为对那些来自英文背景家庭的学生,一开始跟他们讲华语,他们无法听懂就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和热枕。假如先以英语和他们沟通,向他们解释华文字词的意思,然后再慢慢过渡到华语,这样的教学将会更有效。
几十年来,苏启祯的生活重心就是教学、研究及音乐。退休后他出版了七、八本书,都是以英文撰写的,因为出版商不愿意出版华文书。这些书主要是有关教育方面的如《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学力比较》以及《在新加坡华文教学》等,由World Scientific及Springer出版。他根据统计学的分析,发觉原来的世界大学排名,名不符实,因为忽视了8个统计数字的重要指标。苏启祯在书里运用各种实用的指标及统计学检验,指出世界大学排名并不如一般人相信的那样可靠。

上世纪90年代,苏启桢在香港讲课,与夫人李碧玉女士合影
苏启祯与李碧玉女士于1957年结婚,育有一女苏茜、二男苏苒和苏蓁,还有孙男苏鸿和孙女苏鹓,皆已长大成人,在各领域里各有所成。李女士于2016年逝世。如今,苏博士虽然已达80高龄,但对“治学”和“自学”热情不因年龄而减弱。访谈期间,只见他精神奕奕、思路清晰、分析入微、令人信服。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500x383.jpg)
-500x38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