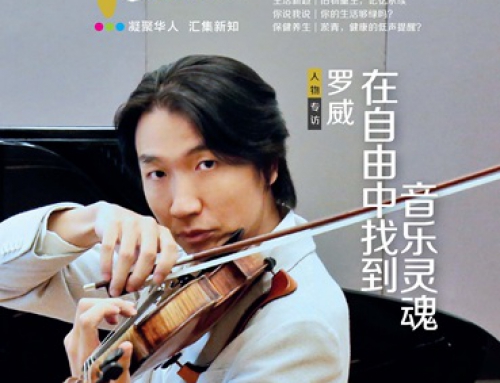棺材街上的马打厝
警署、棺材铺与咖啡店,交织着拘禁、死亡与市井烟火。
文│王振春 图│新报业媒体提供
毕麒麟街(Pickering Street)很长,中间隔着桥南路,上段是大人街,下段俗称棺材街,非常出名。
毕麒麟街出名的原因有二。一是这条街名“毕麒麟街”取自人名,毕麒麟是殖民地时代“大人衙”的总舵主。大人衙是当时的华民护卫署,毕麒麟是华民护卫司,专门管新加坡华人的事务。
毕麒麟街出名的第二个原因是,昔日这条街有几间棺材店,晚上月黑风高时,整条街阴沉沉,加上街灯昏暗,路上很少行人,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叫人心惊胆跳。当时的华人往往把毕麒麟街叫做棺材街。
中学生与政治犯都待过
时过境迁,毕麒麟街早已没有了棺材店,棺材街这个叫法也不复存在。
想当年,毕麒麟街左边的第一间建筑物,高大堂皇,很多人叫它“玻璃马打厝”,也有人叫“一号马打厝”,因为它是中央警署,在殖民地时代的几十个警署里,它是老大,即警察总部,所以民间称 “一号马打厝”。那块地如今已变成珠宝中心大厦。

上世纪50、60年代出殡仪式。以前出殡时运载棺木的罗厘,是采用纸或布制的“棺罩”,以彩色色调为主,往生者身穿古式寿衣,家属披麻衣戴孝。照片是毕麒麟街洪振发寿板店。
其实,“玻璃马打厝”是叠床架屋的一种重复叫法。“玻璃”是英文“Police”的谐音,意即警察;“马打”是马来话的“Mata”,即警察的意思,所以“玻璃马打”是警察一词的重复。“厝”是闽潮琼语“屋子”的意思,“马打厝”意指警察局。
我记得童年时,长辈提起这间警署时,都是用“玻璃马打厝”。当年那些出名的政治犯,都是先关在这里,之后才转送到樟宜监狱。
1962年我在华义中学求学。有一次骑脚踏车上学途径“玻璃马打厝”时,被警察半路拦截,要我进马打厝。我没有犯法,却无端端被拉进马打厝,说不害怕是假的。记得当时被带到一个小房间,和几个人并排坐在椅子上,十多分钟后才打开房门让我们出去。
那天上学迟到了,事后才知道,原来被拉去做“道具人”,跟几个也是在路上被拉去的路人,跟一个嫌犯坐在一起,让门外的一些受害人从门缝里认人。那真是叫人心惊的经验,万一受害人错把冯京当马凉,认错了人该如何是好?
“玻璃马打厝”就在棺材街上。有个姓翁的画家告诉我,1960年代有一次他搭德士到毕麒麟街,好心的司机对他说:“你要到的是棺材街,那边有几间棺材店,叫‘洪振发’的那间很出名,以后你只要讲去‘洪振发’或棺材街,德士司机都知道。”

1958年7月7日至12日举行新加坡警察周时摄。图为中央警署开放,吸引了许多市民入内参观。
帮嫌疑犯买香烟
可见,比起毕麒麟街,棺材街更多人懂,因为当时这条街有不少棺材店。据当时住过毕麒麟街的三哥说,“一号马打厝”的一些窗口,正对着毕麒麟街的棺材店。他曾看到有些被关在“马打厝”的嫌犯,隔着玻璃窗哀求棺材店的伙计,帮他们到附近的咖啡店买香烟,或代打电话回家请家人来保释,而棺材店的伙计通常也会帮忙。
嫌犯获保释后,会买一两包香烟答谢棺材店的伙计。三哥说:“有一次新加坡戒严,整条毕麒麟街,只有一间咖啡店做生意,而且营业24小时,专卖茶水给警署里的警察。”
童年时,我在毕麒麟街住过两天,因为我的三叔,在毕麒麟街有间咖啡店,为了找堂哥玩,我在咖啡店楼上睡了两晚。三叔的咖啡店开在棺材店隔壁,那时的人,谁会一大清早来这里喝咖啡,难怪生意不好,开没多久便关门大吉。

国家发展部曾经坐落在毕麒麟街。
本地首家寿板店是哪家?
1912年来自福建南安的洪诗嘉,在毕麒麟街开设新加坡第一家寿板店,取名“洪振发”。
随着其他同行陆续加入,洪振发的生意也扩大,同一条街拥有七八家店面,毕麒麟街因此有了“棺材街”的俗称。
洪振发寿板店历经百年岁月,如今已发展成洪振茂集团,提供多元化殡葬服务。
以前的棺木…
-800x598.jpg)
从洪振茂寿板店旧时店面的绘图中,可以想象昔日当街制作和摆放棺木的情景。(图源:洪振茂生命礼仪)
以前的中式棺木,最重的超过200公斤,现在的约在65至130公斤之间。出殡时运载棺木的罗厘,是采用纸或布制的“棺罩”,以彩色色调为主。
至于火葬方法,则是用木柴烧棺木,需有人不断在炉底下添木柴,最高温度达300至400摄氏度,需要烧一天一夜。现在使用电气加煤气,温度可迅速升高到900至1100摄氏度,90分钟就能完成火化过程。
此外,那时候的棺材店,除了展示四到六口不同样式的棺木之外,也是囤积树筒、加工木料和打造棺木的地点,因此需要很大的工作场所。因此,毕麒麟街直到六七十年代还保留“棺材街”的俗称。
资料来源:《联合早报》
死人街在哪里?

牛车水死人街
棺材街的俗称因棺材店而起,而死人街也是顾名思义。
牛车水史密斯街(Smith Street)前面有一条平行的硕莪街(Sago Street),开埠初期,这条街有制作硕莪粉的厂。硕莪是一种热带植物,树身粗松,去除外皮后可绞磨成粉当食材。这条街旧时称为“戏院前街”。
随着时代变迁,硕莪厂没有了。倒是旧式的殡仪馆来到了这里,还有前面的硕莪巷,广东人称为“大难馆”,也叫这条街为“死人街”。这条街早年有一座小庙,因此,也叫“庙仔街”。
广东人称殡仪馆为“大难馆”,意指死亡是人生最后的大劫。大难馆也为末期病人设立养病所,就设在大难馆楼上,让临终的老人在这里“熬”时间。
养病所设备简陋,只提供铺着草席的木板床和伙食,在那里度过最后岁月的主要是当地街坊,梳起不嫁的老妈姐,还有一辈子都赎不了身的妓女。也有家长将红包放在垂死的婴儿怀里,遗弃在大难馆门口。
高峰期,养病所一层楼住上十多个病人。能够自理者收费每天1元,无法自理的收块半钱。养病所床位短缺,病人便被安排在大难馆内寄宿。大难馆内分成四个摆放尸体的隔间,出殡前才移到棺材里 。
资料来源:《联合早报》
下期预告:大人街上的大人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