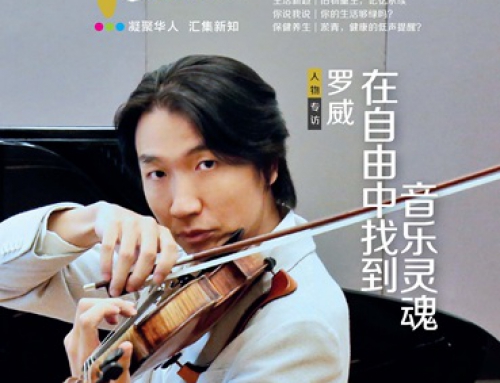百年老街的岁月回响
叮叮当当、砰砰咚咚的敲打声不再响起,取而代之的是车水马龙的时代节奏。
文│王振春 图│档案照、新报业媒体提供
烈日下重访美芝路三条百年老街。
岁月沧桑,老街已经完全变了样,旧的店屋早已不在。走进老街,脑海里依然跳腾着打铁、打铜和打石的声音,这三条老街,便是昔日远近驰名的打铁街,打石街和打铜街。
打铁街的官方路名是苏丹门(Sultan Gate),隔壁的打石街是彭亨街(Pahang Street),这两条街彼此相邻,犹如一对姐妹花,曾经光芒四射,大家都知道美芝路铁巴刹附近,有打铁和打石两条老街。从这两条老街走出来,前面是长长的苏丹街(Jalan Sultan),苏丹街便是打铜街。
这三条老街,对新加坡早期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彭亨街(Pahang Street)一带以前俗称“打石街”,是许多石匠聚集制作墓碑和磨坊的地方。
打铁街的兴衰更迭
那年头,附近有两所知名的华文小校——崇正和崇本。前总统王鼎昌和前国会议员王世丰,便是崇正学校的校友。这间小学如今已搬迁到淡滨尼市镇。崇正的隔邻是崇本。崇本原是华文女校,1980年代末,随着时代变迁,消失在教育改革的洪流中。
这两所学校的前面,有个篮球场,我小时候就在那里打球。那天走访老街,崇正的校舍还在,墙壁上还有几个字“1938,虎豹礼堂,崇正学校”。原来校舍是在1938年,由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出资盖的。时过快百年,字迹被岁月吞噬,但还隐约可见。
崇正的不远处,便是打铁街。
童年时代,曾陪母亲到打铁街一间咖啡店补牙,我们住在海南街,附近就有几间补牙店,但母亲还是搭三轮车,舍近就远,到打铁街补牙。原来,打铁街那个补牙师父,是父亲的同乡老友。记得有一次,母亲补好牙后,他带我们进打铁店,看打铁匠打铁,从交谈中才知道打铁是一门大学问,也略知一些打铁的步骤。
每间打铁店都有一个大火炉,炉边有一个风箱,风箱一拉,风进火炉,炉内便冒出熊熊烈火。
打铁师父站在火炉旁,怕被火烫伤,肩上围着一条毛巾,用结实有力的双手,把铁料烧红,然后用左手夹出火红的铁块,放在铁板上,右手举起小锤,把铁料打到由红变暗,然后再放进炉里烧红,经过反复多次,才打成大小弯度不同的铁具,如锄,刀等,成形后,再次烧红,浸在水里或丢进炉渣灰里冷却,最后,再拿磨刀石磨至锋利。
民间常用的菜刀、锅、锅铲、刨刀、门环、门插、钩、锄、剪刀等,都是这样打造出来的。要吃打铁这口饭,一定要吃得苦中苦。
这几年,导游也带旅客到打铁街和隔壁的打石街来,这里和牛车水一样,有新加坡昔日的历史,早期的海人*,就曾住在这一带。
.jpg)
早年许多经营墓碑雕刻生意的店家,都聚集在甘榜格南的惹兰苏丹和彭亨街, 匠人端坐碑石前,以一手标准的书法仔细描摹后雕刻。(摄于1987年10月)

彭亨街(Pahang Street)一带以前俗称“打石街”,是许多石匠聚集制作墓碑和磨坊的地方。
那天,带着怀旧的心情,希望能在曾经的打铁街找到昔日那间咖啡店。几十年前,便曾陪着妈妈到咖啡店的楼上补牙,结果当然大失所望,打铁街完全换了新貌,街上冷冷清清,一整排的打铁店早已烟消云散,一间咖啡店也没有。
打铁街有两段黄金时期。一段是1948年间,英军重返新加坡,各行各业开始复苏,重建新加坡,处处需要到铁,因此铁的需求量特别大。
另一段时期是1963年8月31日,马来西亚诞生,遭到印度尼西亚对抗。1965年3月10日,印尼特工在乌节路的麦唐纳大厦放置计时炸弹,导致二死33人被炸伤。印尼以前时常卖铁器给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抗后,进口的印尼铁器断市。
印尼的铁进不来,正好给本地打铁行业,带来兴旺的机会。于是打铁店应时兴起,一间间成立,苏丹门变成了打铁业的世界,触目所见都是打铁店,耳边响起的,尽是“叮当叮当”的打铁声。
那年头,因为打铁业的兴起,也带来了一首打铁歌:“早打铁,晚打铁,打一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一歇,我不歇,我要回家去打铁”,读书时男女同学谈恋爱,也叫“打铁”。可见那个年头,打铁行业的兴旺,“打铁”两字,成了民间的口头弹。
打铁行业如日当中,原因是各行各业都要用到铁,比如海上的舢板,船针很重要,只有到打铁店来,才能买到船针。造船业也开始动起来,需要大量的铁器,当然也要来打铁店。星马两地胶园用的胶刀,都是铁器。1959年自治邦成立,政府大兴组屋,裕廊工业区大盖工厂,也都不能没有铁。于是打铁行业如雨后春笋,成了那时一支独秀的宠儿。

曾经铁匠的敲打声是苏丹门一带的背景音乐,然而经过80多年的演变,坚持下来的只剩下一家
“李来兴”。2007年店铺在火患中烧毁,结束营业,打铁街正式走入历史。图中是最后的打铁匠李亚成。(摄于2006年)
然而好景不常在。1970年代,舢板被时代淘汰,造船业的铁器已有工厂制造,胶园的胶刀,马来西亚自己能生产,新加坡的打铁行业江河日下,黯然无光。
打石街的昭南岁月
从打铁街拐个弯,便是打石街。
打铁街和打石街是邻居,看着美芝路的千变万化,也见证了不远处的铁巴刹走入历史,一般走进打铁街的人,大多也会顺道逛逛打石街。
打铁街风起云涌的年代,打石街也一样大放光芒。
打石街曽是海人的甘榜,海人离开后,留下的地方是潮州人雕刻墓碑的打石铺,其中印象深刻的是顺发永记石铺。
1960年代,母亲带我到打铁街和打石街时,整排店屋都是铁铺和石铺,人来人往。1980年我走访打石街时,只剩两间石铺。回忆过往,石铺老板摇头叹息。一年后旧地重游,打石店已完全消失了。
打石街生意最好的年代,应该是昭南岛时期。
日军占领新加坡三年八个月,苦不堪言,那时打石业忙得团团传。因为当时米粮不足,只有木薯最多,于是小市民只好吃木薯充饥,木薯要用杵臼来捣,杵臼是石头做的,家家户户吃木薯,便要到石铺买杵臼。后来,杵臼慢慢少人用,改用石磨磨糙米。再后来,吃木薯干的人少了,磨米的时代也过去了。
打石街附近有间马来回教堂,也是打石店兴旺的原因。回教徒逝世,回教堂为他们办葬礼,死者的墓碑大都请打石匠造作。据说印尼和文莱,也有不少订单给打石店。
昔日岛国都是土葬,也给打石匠带来很多生意。现在流行火化,海葬也开始了,已不需要打石匠,对打石行业来说,是个打击。
*“海人”是指生活在沿海或靠海为生的原住民群体,包括捕鱼、采集海洋资源、航海或从事海上贸易的群体,大多是马来人或海上游牧民族。

Pahang Street,曾经的打石街
打铜街的三个叫法

Jalan Sultan,曾经的打铜街。
老一辈的华人,读书不多,不习惯苏丹街的英文名叫法,于是按这条街的特质衍生出三个叫法:打铜街、二十间与电车弯。
每个民间叫法,都有其渊源。
打铜街,顾名思意,因为这条街有很多打铜店。
二十间,是因为这条百年老街,昔日很多古老的店铺都拆了,只剩下二十间,打铁街兴旺时,有几间打铁店找不到立脚处,也跑到打铜街来,铜铁一家,陪伴着苏丹街 。
至于电车弯,則是因为以前有轨电车从小坡大马路直走,终站是惹兰苏丹。所以惹兰苏丹人称电车弯。
苏丹街的官方路名是惹兰苏丹,因为附近有间苏丹王府,建于1836年到1843年之间,车辆进出都要经过这里,所以也叫苏丹街,附近的打铁街,叫苏丹门。那时的苏丹,风光一时,苏丹王府里住着苏丹的子子孙孙,皇亲国戚。苏丹王府前的道路上,挂了一个牌,写着“甘榜格南王府”几个字,因为王府所在的地方,便是甘榜格南。甘榜格南也曾是马来族的聚集地。
时过境迁,烈日下到三条百年老街走透透,瞬间思绪飞扬。打铁、打石和打铜的行业早已看不到,看到的是岁月无情的变迁。
下期预告:余东璇街的今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