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狮城文人
文图·胡春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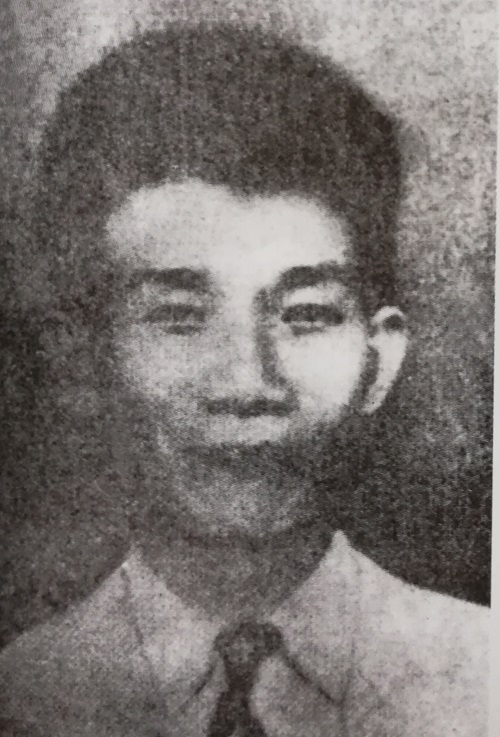
郁达夫1940年在新加坡
新加坡开埠以来,许多中国名作家南来落户,如胡愈之、老舍、徐悲鸿、王任叔等,郁达夫就是其中之一。郁达夫对待狮城的每一位文人作家都很亲切和谦虚,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绝不会因为自己是大作家而摆架子。据当时与郁达夫同室办公的记者兼《星洲晚报》电讯编辑吴继岳回忆时记述,他的办公桌与郁达夫并排,彼此相处融洽,无所不谈。郁达夫为人和蔼可亲的性格与骄傲无比的主笔关楚璞真是天渊之别。若要摆架子,郁达夫比关楚璞更有资格,但郁达夫不摆架子,他对报馆里的同事一视同仁,因此颇得同事们的敬重。

40年代位于罗敏申路的星洲日报报馆,是郁达夫工作的地点
郁达夫来新加坡的工作是,除了撰写时势评论,还兼任文艺副刊《晨星》的编务。他上班的第二天《星洲日报》时事评论版刊出《为努力宣传抗战,郁达夫将入本报工作》,以醒目的标题为报馆的声名大力宣传。而郁达夫接编的第一个《晨星》版在1939年1 月9日见报,他写了一篇《晨星的今后》述说道:“《晨星》这块小园地,若能在星洲,在南洋各埠,变作光明的先驱,白昼的主宰,那岂不更是祖国之光?人类之福? ⋯⋯希望由本刊的这一角小园,培植出许多可以照耀南天,照耀全国,照耀全世界的大作家。”由此可看到,郁达夫来狮城是怀抱着伟大理想的。因此,郁达夫在《星洲日报》担任编辑3年又2个月的时光里,写作甚勤,共发表462篇文章,深受狮城文人作家的敬重,其文学成就带动了当时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两地的华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只可惜郁达夫的伟大理想因战乱而没有完全实现。

郁达夫不但是文艺副刊主编,他在美术方面也有一手,《晨星》版版头就是他亲手设计的
才华横溢的郁达夫在旅居新加坡的时候,常与狮城文人、作家、画家、音乐家等交往甚笃。以他的性格来说是谦虚与亲切的,因为他对于文艺青年寄以厚望,所以,在他旅居新加坡的3年当中,非常热心的与文艺青年走在一起,即使工作忙碌,他也会抽出时间接见他们。在他中峇鲁的寓居,客厅里悬挂了一幅徐悲鸿的奔马图,优雅的气氛下,经常可以见到一大批文艺青年围聚聊天,而郁达夫总会对他们说些劝进、鼓励的话。比如针对爱写小说的初学者,郁达夫教他多读法国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的作品。在苗秀的著作《马华文学史话》的文章中,有记述:“郁达夫非常喜欢接近文艺青年,他那时候的寓所在中峇鲁,笔者不止一次到过他的寓所。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觉得他的性格平易近人,毫无半点大作家的架子,对我们这些前去拜访的喜爱文学的青年人非常欢迎,态度也极为诚恳,对于年青的写作者,他的奖励更是不遗余力。”苗秀是经常投稿《晨星》的作者,也是常到郁达夫寓所做客的文艺青年之一。苗秀后来在1947至1950年主编《晨星》。
另一个经常去郁达夫中峇鲁寓所的文艺青年是费朗,他在《记郁达夫》中回忆说,他每一次去,都看见郁达夫那个十三四岁的大儿子郁飞,常常独自坐在屋角的梳妆台边,手拿着一本当时很盛行的一折书《东周列国演义》很专心地读着。他说是他父亲叫他看的。郁达夫告诉费朗说:“对于初学作文的人《东周列国演义》很有价值,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费朗很不解,这本不文不白的章回小说对一个少年在写作上会有何益处?后来细想一番,也许郁达夫是受林语堂的影响吧。
郁达夫在例常的聚会上,常常扮演导师的角色,他要求文艺青年在写作技巧上应注意文字的修辞。他发现文艺青年在文笔这方面的表现过于呆板,不理想,原因出自他们平时少看书、少思考的缘故。所以他一直勉励文艺青年需常深入社会群众的生活,多观察多体会,在文笔和思维上多锻炼。根据当时在报馆里负责校对的一位职工何克坚写的《忆郁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很多学生和青年投给《晨星》版的稿件,都经过郁先生的修改,而且红字红线很多,甚至有些文章已被删了一大半,这种情形,老实说如果遇到其他编辑,恐怕早已被丢进纸篓里去了。”由此可见,郁达夫是个很爱惜人才的“导师”,是非常有耐性的、很仔细的批稿而不轻易把不满意的稿丢弃,目的就是为了栽培文艺写作人才。唯一使他纳闷的是,狮城与吉隆坡、槟城都是华人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但投稿者当中,狮城和吉隆坡两地的作者最多,槟城反而是最少的。
另一方面,郁达夫说学生与青年少看书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七七事变”发生前后,中国出版的刊物很少,即便出版物能运到南洋也是被禁的,狮城也不例外,所以文艺爱好者很难有机会阅读到较好的书刊。基于此,郁达夫就利用报章的版位刊登中国大陆知名作家的作品,如鲁迅、老舍、丁玲、茅盾等,这样一来可提高副刊文艺作品的水平和分量,也给文艺爱好者一个学习借鉴的机会。
郁达夫在主编《晨星》期间,因为经常收稿、批稿的关系而结识了许多狮城文人作家、文艺青年、知识分子,对他们可谓关怀备至。此时的郁达夫生活条件很好,他在报馆每月领的薪水是叻币200元,是属于第二高薪级,因此,他有能力经常邀请文人作家和文艺青年到他家里去雅聚,给文艺青年看稿、改稿、谈写作技巧、提供建议。凡有优秀作品,他都对作者连赞不迭,文艺青年们因此受到很好的引导和鼓舞。像他这样的作风,在今天还是少有的。根据记载,郁达夫培养的一批文艺青年有刘思、漂青、辜石如、林英屏、艾蒙、金石声等。刘思后来成了狮城著名的诗人,艾蒙(后改笔名林晨)成为知名的剧作家。其他在40年代初的本地知名作家,如铁抗、王君实、倩子、冯蕉衣等人,也通过不同的方式与郁达夫直接或间接接触,他们都深受郁达夫倡导的文艺思想的影响而精进于创作。据说与郁达夫接触较频繁的是铁抗,因为铁抗也在报馆工作,机会自然比别人多,但是后来铁抗不知何因,辞去报馆的工作,自己跑去加东一栋小楼上隐居,面对加东海滨日以继夜地写他的长篇小说《无火灾地带》。不久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也沦陷了,铁抗在日本法西斯大屠杀中牺牲了,他那本长篇小说也不知去了哪里。
宗教界的文友释广洽法师还记得郁达夫在写作时,左手拿着酒瓶,右手拿着笔,也不用什么酒杯,一边喝酒,一边写诗,态度闲适之极。有一次释广洽法师问他离婚了怎么办?郁达夫很爽朗地回答:“我写诗送送她,跟她握握手。”释广洽评价郁达夫“是个洒脱之人,有学者之风,不摆架子,也无宗教色彩。我能与他相识,实在是缘份⋯⋯回想当年情景,恍如隔世。”
与郁达夫一起乘船逃难印尼的好友胡愈之,对郁达夫的评议发表在1947年8月29日新加坡《南侨日报》之《南风》版上。胡愈之写道:“郁达夫不是什么伟人,更不是一个革命家,但他可算得近代中国少有的一个天才诗人。他的作品应当在中国文艺史上,永远保留一个地位⋯⋯在一百年、两百年之后,郁达夫这个名字是不会被我们后代所完全遗忘的。 ”
温梓川,也是郁达夫的好朋友,但温梓川自述他在郁达夫旅居新加坡期间,并不常见面,各自分开忙着,但他常收到郁达夫的来信,鼓励他多写。于是,温梓川寄了一篇5000字的小说,郁达夫用一版全篇刊完。从来不在稿末打上“未完”或“待续”字眼,这是郁达夫编辑的作风。对于温梓川的短篇小说作品,郁达夫认为《阿松伯的生日》堪称杰作,《罪与罚》也是很优秀的传奇性短篇小说。
郁达夫旅居新加坡的时候,除了忠于职守,在社会上接触面也很广,对狮城民生的体验与观察也较深刻。他很积极地推展新马文艺,尤其对狮城的文艺青年有殷切的期望。郁达夫可说是这群南来作家当中,风范独特、文艺生活十分丰富多彩、影响力度深广的一位作家。然而,郁达夫经常很谦卑地表示,他初到狮城,还没把生活心态调整过来,他对狮城的市民生活习惯和方式,都还不熟悉,但他会努力适应。他对南洋的榴 、红毛丹、娘惹、沙爹等食物很感兴趣,曾多次品尝。在报馆接收的投稿中,他看到了狮城青年学生的学习态度、文人作家的思想抱负。郁达夫在新加坡极力倡导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同时,也鼓励作家以南洋色彩、本土化的有利环境创作文艺作品。他经常对文艺青年强调新加坡的文艺作品应该具备南洋地区的特殊性。
郁达夫在接手编《晨星》副刊时,与狮城一些文人作家因为《几个问题》引发了一场笔论,让某些人对他的印象打了折扣。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闹别扭而导致离婚,也让郁达夫身陷寂寞,下班后经常打麻将、去南天大酒楼饮酒跳舞、与女人聊天、或写些颓废诗,因此,有一些对郁达夫心怀妒忌和思想比较激进的文人作者,讥笑他是逃难作家,撰文与他笔战,骂他落伍,甚至以《沉沦》那篇小说诬蔑他是个黄色文艺大师,这些无理的指责,他从不回应。
与郁达夫常聚在一起的胡愈之,1940年南来狮城担任《南洋商报》总编辑,对此类评语则有很中肯的说法:“没有亲近郁达夫先生的人,都以为郁达夫生活是顶浪漫的,待到和达夫在一起之后,才知道他的生活顶严肃的,他对工作又是非常勤谨的,不然,等身的著作将何而来?”

郁达夫在新加坡留存的墨宝不多,除了虎豹别墅门前的对联,“星洲书店”也是其中之一
郁达夫寓居新加坡3年的生活是充实而精彩的,他除了勤于写作,同时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协助宣传抗日、筹赈经费、推展华文文化活动。在狮城,他一直是以文艺战士的姿态在华侨社群中坚守爱国、救民族的岗位,所写的各种题材的文章、诗词,数量多达400多篇,散见于新马报刊杂志上。诚如方修所说的,这是“郁达夫留给本地的一笔文学遗产”。1945年,日本侵占新加坡时,郁达夫忙于抗日活动,最终碍于局势紧急,不得已与几名文友逃离至印尼苏门答腊过着流亡生活,后不幸遇难,无法再回返新加坡。如若不然,郁达夫对新马文坛的推动与发展,肯定更有一番大作为。
(作者为本地作家)


-500x383.jpg)
-500x38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