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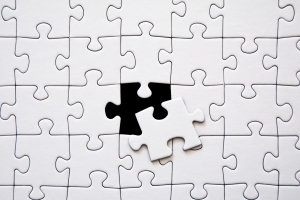
1987年开始,除了特选中学之外,新加坡全面落实英语作为第一教学媒介语的语文教育政策,华语教育自此进入第二语文的时代。华语作为二语之后,有关华语程度在新加坡日益下降的评论之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不少学者也针对这个课题进行必要的研究与探讨,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例子之一是两位学者谢世涯、苏启祯在1990年代初期共同进行的两份研究报告:《认字辩词与阅读理解能力》和《构词能力与偏误分析》中所指出:读了十年或十二年的中四或初级学院的学生,无法读懂有关政治、经济、贸易、投资协定、国际动向等的报章文字。(见谢世涯《商业华文课程的编制与教学》,1997年11月《中教学报》第23期)有鉴于此,谢世涯当时就起草了一套商业华文课程的编制与教学大纲。
1998年,学者吴英成在《华文实习教师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研究》中指出:即使未来要担任华文老师的新一代双语人,他们在交谈的对象、交际的场合、讨论的课题、不同语言的媒体、中英语言的工具与文化价值等方面,也跟其他年轻族群一样,皆是以英语为主,华语为副。(见周清海、吴英成《短刃与长剑齐舞——第20届讲华语运动的新起点》,1998年9月21日《联合早报·言论》)
吴英成关于“华文教学师资在质量上的危机”的隐忧,与资深教育工作者谢泽文不谋而合。2000年6月,谢泽文在“第九届国际汉语语言学会议暨国际华语教学研讨会”上宣读《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与华文教学》一文时指出,新加坡华文教学所面对的三大挑战是:学生缺乏学习华语的积极性;如何利用资讯科技改进教学;如何培训和招聘足够的华文教师以应付未来的需求。
关于培训和招聘华文师资的问题,过去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所采取的是本土培养与国外输入相结合的方式;关于利用资讯科技改进教学的挑战,在资讯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至于学生缺乏学习华语的积极性,我们或许可以寄望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商贸机遇的大环境改变。
我最近重温了《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与华文教学》和华文教育政策研究者梁秉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1965-2005》一文,对于影响新加坡华语教育生态深远的六份报告书,做了一次回顾式的巡礼。
第一份报告书是1956年出炉的《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1955年4月,鉴于华校中学生反殖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有由学潮蔓延成工潮之势,英国殖民地政府在5月间设立了“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负责检讨当时的华文教育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委员会主席是时任教育部长周瑞麒(劳工阵线),八名委员包括时任地政与建屋部长哈密裕末(华巫联盟)、劳工与福利部长林有福(劳工阵线)和李光耀(人民行动党)等。
报告书针对双语教育的主要建议有:平等对待各语文源流的学校;各语文源流学校至少教导英文、马来文、华文和淡米尔文这四种语文中的两种;各源流学校须采用共同的课程标准。这也是新加坡第一次提出“双语教育”的概念。所谓双语教育,是指在英校教导马来文、华文或淡米尔文,在马来文、华文和淡米尔文学校教导英文。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沿用报告书中关于双语教育的建议。
第二份报告书是1963年8月公布的《新加坡教育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委员会主席是时任新加坡大学副校长林溪茂,因此报告书也称为《林溪茂报告书》。它主要是针对第一份报告书中诸项建议的实践成效做出检讨及提供修正意见。
第三份报告书是1979年2月公布的《1978年教育部报告书》,也称为《吴庆瑞报告书》。1978年8月,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庆瑞领导一个教育研究小组,全面检讨教育部的运作系统和教学问题,并提出改革方案。报告书全面检讨了当时的教育体系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损耗率,也就是辍学率和不及格率。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的建议,便是针对这个问题而做出的。
在分流制度下,学生小学毕业后,根据会考成绩修读不同程度的中学课程。特别课程班英文和母语都应该达到第一语文的水平,快捷课程班修读英文第一语文和母语第二语文的课程,普通课程班修读水平较低的英文第一语文和母语第二语文的课程。
第四份报告书是1992年3月公布的《新加坡华文教学的检讨与建议:华文教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也称为《王鼎昌报告书》。1991年,时任副总理王鼎昌负责检讨学校的华文教学,并提出改良建议。报告书建议把华文第二语文称为“华文”,把程度较高的华文第一语文称为“高级华文”,以符合大部分家长和学生的意愿;提前教导汉语拼音;让更多学生修读华文第一语文;重新编写教材。
第五份报告书是1999年1月公布的《李显龙副总理政策声明》。为了应对新加坡语言环境的改变,1997年至1998年,政府成立了以时任副总理李显龙为首的检讨华文教学委员会,启动教改以规划将来发展。报告书建议:确定华文的教学目标;鼓励更多学生修读高级华文;重新编写教材并修订考试方式;帮助学习华文有困难的学生。
第六份报告书是2004年11月公布的《华文课程与教学法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为了谋求华文教学新的发展方向,政府在2004年2月委任“华文课程与教学法检讨委员会”。报告书建议,华文第二语文的教学应注重有效的口语交际及阅读训练,尽快让学生掌握听、说、读的能力。由于去掉了对“写”的要求,梁秉赋认为,这次的教改象征着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经历了另一个重大的阶段性改变。
上述六份关涉新加坡双语教育变革的报告书,让我们看到了华语二语教学在新加坡发展进程中的几次重大分水岭。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全球掀起中国语言文化热,促进了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的复兴。2005年6月,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与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许琳签署“合作建设孔子学院协议书”。2007年7月,南大孔子学院正式开幕,由内阁资政李光耀主持典礼。李资政当时说,过去40年来,新加坡实行双语教育,累积了华语二语的教学心得,是我们在汉语教学方面的优势。
2008年9月,李显龙总理在《联合早报》85周年晚宴上宣布成立“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2009年11月,华文教研中心由李资政揭幕。它以“提供优质教研培训,加强华语言文化学习,建立新加坡华文教学品牌”为使命,成立后积极招聘专家,展开工作。第一阶段设计81门华文教研课程,并定下一年内培训千名在职华文教师,五年内培训四千名华文教师的指标。
南大孔院和华文教研中心的先后成立,具有明显的导向性意义,使新加坡拥有世界最庞大的华语二语教学与研究实验场。2020年8月,《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十五周年纪念特刊2005-2020》出版,梁秉赋院长在《我们的成长》一文中,强调了华文教学在新加坡的机遇。他认为,南大孔院除了致力于为新加坡各界提供普及性的汉语教学外,更以进一步提高新加坡社会对规范化中文的掌握能力,及深化新加坡华族文化底蕴为最高目标。这意味着如果孔院发挥得当,将能够提高新加坡在华文教学方面的既有优势,同时把新加坡的教学经验贡献给全球因孔院而带动的汉语学习热潮。
2020年9月8日,在华文教研中心举办的“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与学”线上国际研讨会上,教育部长黄循财在主持开幕仪式时,以华语强调母语的学习与应用不该局限于校园内,华族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努力学习华语。这是政府坚定与贯彻双语教育政策的又一次表态。
梁秉赋对于新加坡华文教学的机遇的乐观认识,虽然是以南大孔院为本位,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华文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八九十年代之交,本区域的一些国家如缅甸和越南逐步调整政策,华文教育环境相对宽松,也给依托英语背景的新加坡华语二语教学带来了启示和机遇。
1980年代末期,由于中缅边界贸易频繁,缅北地区对华文教育需求较为迫切,各类华文学校获得地方政府的许可,纷纷开办,不少缅甸人也将子女送到华校学习。一些家庭补习班合并和扩充,华人社团以补习班的名义开办华文学校,有的规模达到了数百甚至上千人。
1992年颁布的越南宪法第五条规定:“各民族有权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维护民族本色和发展本民族美好的风俗、习惯、传统和文化。”自此,越南华人积极抓住机遇,通过多种举措推动母族语文教育的恢复发展。据知,目前越南华人的华文教育形式主要有三类:一、附属于普通中小学、教学上相对独立的华文中心;二、越南华人个体或社团筹资兴办的越华双语学校;三、面向需要提高华文水平的职场人士,突出华文的实际运用,并开设电脑、商贸、会计等职业技能培训的华文培训班。
由于长期生活在讲缅甸语和越南语的土地上,华语于缅甸与越南华人可能只是二语甚至三语水平,这种经历与新加坡华人极为相似。因应环境的改变,新加坡在七八十年代经历了从华校到英校的转型;再用数十年的时间,使得华语二语教学成为这片土地上亮丽的景观,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文化品牌。对于这个品牌而言,对华文学习存在强劲需求的东南亚其他国家是不可忽视的庞大市场。
space
(作者为新加坡业余写作人)
space


-500x383.jpg)
-500x383.jpg)


